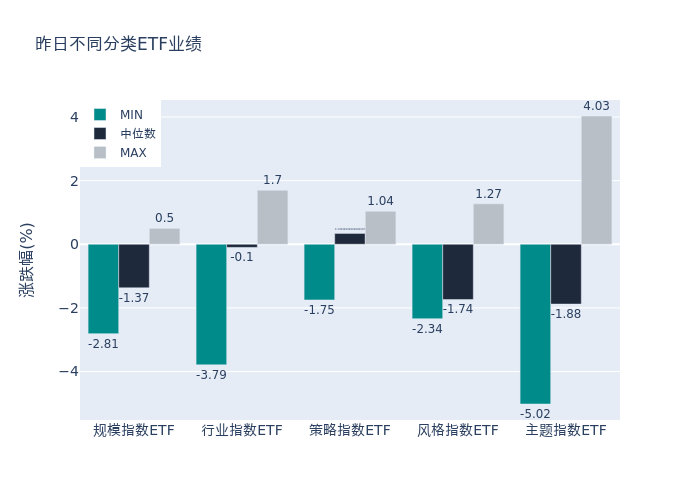【专题】龚刚|中国现代文论(一)钱锺书的悲剧观
作者简介龚刚,1994年起于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后于清华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师从戴锦华、乐黛云、万俊人教授,现任澳大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学术总監、中文系博导、《澳门人文学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伦理叙事学;比较诗学。著有《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及散文与文学批评合集《乘兴集》(作家出版社)等,主编有《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华文史论丛》、《伦理学研究》、《人文中国学报》(香港)、《钱锺书诗文丛说》(台湾)等学刊或论文集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另在《中国学术》、《中华读书报》、《散文》、《诗刊》、《香港文学》等报刊发表诸多书评、译文及各类文艺作品。
钱锺书的悲剧观龚刚
钱锺书的悲剧观集中体现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中,其《谈艺录》(1984修订本)、《管锥编》(1986)中论及悲剧的片段,基本延续了他早年的观点。
钱锺书认为,“戏剧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悲剧,中国戏曲家恰恰在悲剧创作上是失败者”,因此,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并没有真正的悲剧。[1]理由有三。首先,在中国的严肃戏曲中,“诗性正义总会得到体现”;其次,欠缺“悲剧性要素”,如崇高的悲情,“哦,在我的胸间栖居着两个灵魂”的意识,关于片面之善导致普遍之恶的认知等;其三,“虽说大量中国古代戏曲在悲凉的氛围中结束,但敏感的读者仍然很容易体会到它们与真正的悲剧的差别:当他看完这些作品后,并没有获得投入地付出激情或像斯宾诺莎所谓体认到永恒的命运后的平静,而是被个人的刻骨而无助的失落之痛所萦绕,以致难以自拔。”钱锺书以诗性正义总能得到体现作为否定中国存在悲剧的依据,正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对中国古典戏曲追求诗性正义、未体现永恒正义、因而没有真正悲剧的批评相呼应;他所谓“胸间栖居着两个灵魂”,应当是指悲剧主人公内在意志的冲突,也就是他后文所说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对抗”;他所谓真正的悲剧应该让人最终获得平静而不是沉溺于痛苦,显然是从观众接受和悲剧效果的角度立论,在他看来,悲剧可以唤起观众的激情,但这种激情最后应当在体认了永恒的命运之后趋于平静,这和前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一脉相承,因此,如果一部戏剧仅仅表现了个人的苦难并令观众痛苦萦怀,就不能称之为是悲剧,这就为区分悲剧与惨剧、苦难剧、悲情剧等同样表现主人公不幸遭遇的剧作类型提供了有效的判断标准。
在点明了中国的严肃戏曲何以不是悲剧的理据后,钱锺书又以莎士比亚和德莱顿的悲剧《安东尼与克丽奥帕特拉》(约1607)与《爱是一切》(1678)为参照,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的代表作《梧桐雨》、清代著名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该剧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并称清传奇“双璧”)为何不是真正的悲剧。他指出,《梧桐雨》、《长生殿》表现的都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正如《安东尼与克丽奥帕特拉》与《爱是一切》表现的都是古罗马统帅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的故事,而且它们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在阅读这两部中国戏曲的过程中,“读者的个人化的同情感并未升华到更高的经验层次”。《梧桐雨》的强烈抒情性和《长生殿》的缱绻情韵,均不能和“悲剧的力量”相混淆。它们没有给读者带来和解,而是使读者的意志最终因代罪者的苦难而被削弱,并在内心的刺痛中吁求慰藉或援助,以及一个“更接近内心愿望的世界秩序”。
[白朴,(1226年—约1306年),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
[早期油印本《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简称《梧桐雨》),白仁甫撰,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点]
[洪升《长生殿》书影]
钱锺书援引英国批评家瑞恰慈在《文学批评的原则》(1924)一书中的观点指出,《梧桐雨》和《长生殿》这样的戏剧情境显然与充分的悲剧体验相距甚远,真正的悲剧体验应当是“无胁迫感,无安慰感,独对众生且无待他求”的一种精神状态。中国戏曲却令读者渴望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而并未给人“一切事物都难免苦涩结局之感”。这些戏曲的结构特征强化了这一阅读印象。它们在表现了主要的悲剧事件之后,还不忘对悲剧事件的后果加以交待。伴随悲剧时刻的最高激情和最深痛苦因帷幕迟迟未落下而被弱化。这就造成了一种颤音或叹息般的拖长效果。例如,在《梧桐雨》中,杨贵妃死于第三幕,唐明皇在这一幕中始终陷于悲叹之中,形容憔悴,破碎的心灵被无奈的忧伤所蚕食;在《长生殿》中,出现在第二十五出的玉环之死只是为第五十出中幸福的重聚所做的铺垫。
钱锺书进而指出,《梧桐雨》和《长生殿》中的戏剧情境未能带来充分的悲剧体验的更重要原因是,“读者无法超越对悲剧人物的个人化的同情,因为后者没有伟大到足以令读者和他们之间形成足够的心理距离。”他指出,在这两部戏剧的主要人物身上确实存在着“悲剧性缺陷”,但它并未与任何以人格的重量或人物的力量加以践行的明确信仰发生关联。例如,作为男主人公的唐明皇本质上是一个懦弱、无能且近乎自私的肉欲主义者,他几乎不敢进行抵抗。他也没有“内在冲突”之感。他因为爱杨贵妃而失去了江山,然后为了重新赢得江山而放弃了杨贵妃。他的性格不足以使他承受“两个世界的紧张对抗”;他甚至没有“衡量两个世界以确定价值高低的意识”。在《梧桐雨》中,他整个就是一个懦夫和无赖的形象。例如,在叛军的逼迫下,他对杨贵妃说:“妃子,不济事了,寡人自身难保。”在《长生殿》中,唐明皇还真显示出几分勇气。当杨贵妃准备慷慨赴死之际他还出言阻止说,他宁愿为了爱而失去天下。但在犹疑观望之后,他还是把她交给了叛军,并诀别道:“罢罢,妃子既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钱锺书认为,洪升笔下的唐明皇的这番话显然是渗透着血泪的,也可想见他捶胸顿足的苦痛神情,但依然无法和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丽奥帕特拉》与德莱顿《爱是一切》中的安东尼的动情告白相比拟。在莎士比亚笔下,安东尼在生死抉择中咏叹道,“让罗马熔化在泰伯河里,巍巍的帝国大厦塌下来好了!这里是我的生存之地。”在德莱顿的剧本中,安东尼的表述更直白:“把一切都夺走吧,对这个世界我毫不关心!”钱锺书认为,把唐明皇与安东尼的告白相提并论,简直就是“批评的丑闻”,意为悍勇决绝、不惜殉情的安东尼令懦弱的唐明皇相形见绌。他总结说,唐明皇式的临危贪生和难以自拔的忧怨并非悲剧性的体现,但马嵬坡事件的相关情境已经包含了“充分的悲剧性要素”,只是中国古典戏曲家在处理这个情境时没能提供给读者“完整的悲剧体验”。
[约翰·德莱顿(1631-1700)]
在对照分析了上述两组同样表现帝王生死恋的中西戏剧文本、并随之否定了王国维的《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论断(下一节将予申论)之后,钱锺书又援引英国表现主义美学家雷德(Louis Arnaud Reid)的悲剧类型论,对中国古典戏曲加以辨析。雷德认为,悲剧有两类。在第一类悲剧中,人物性格是聚焦点。在第二类悲剧中,命运自身成为关注点。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即属于第一类,而古希腊悲剧则属于第二类。钱锺书认为,中国古典戏曲中那些勉强可以称为悲剧的作品比较接近于“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和莎剧一样,它们不遵循“三一律”,而突出“剧中角色”及“他们对邪恶境遇的反应”。但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所有这类戏曲的作者对于“悲剧性缺陷和冲突”(tragic flaw and conflict)都缺乏充分的意识。
钱锺书指出,雷德的《美学研究》一书中关于悲剧的清晰论述使他“获益良多”。《美学研究》初版于1931年,原名为“A Study in Aesthetics”,钱锺书误为“A Study of Aesthetics”。[2]该书第十三章第三、四、五节分别从悲剧心理、悲剧类型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三个角度探讨了悲剧美学。第四节的标题为“两种类型的悲剧”(The Two Types of Dramatic Tragedy)。钱锺书对雷德的悲剧类型论的引介,主要以此为据。雷德指出:
悲剧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痛苦、不幸、灾难,尽管悲剧必然包含这些元素。车祸、凶杀这些在新闻报道中被称为悲剧的事件,其实不应贸然地称之为悲剧。我们的关注焦点不仅仅是罪恶,而是从罪恶中呈现出的善本质。这种对恶中之善(good-through-evil)的关注主要有两种方式,正好与悲剧的两种主要类型相契合。在第一类悲剧中,人们聚焦于人物和他对邪恶境遇的反应。在第二类悲剧中,境遇或命运本身成为关注点。[3]他又指出,在莎士比亚悲剧中,“人物既要面对邪恶,又被卷入了邪恶之中”[4],而在古希腊悲剧中,“超人力的命运决定了事件的结果”[5]。但是,在这两类悲剧中,都会有“伟大而永恒的价值”(tremendous and permanent value)在冲突中显现,这是悲剧艺术的“独特结构”(peculiar structure)。[6]换言之,悲剧性冲突的本质就永恒价值对邪恶境遇或盲目命运的挑战,莎士比亚悲剧表现的是前者,古希腊悲剧表现的是后者。钱锺书认为,《梧桐雨》、《长生殿》等中国严肃戏曲类似莎剧,却没有深刻表现悲剧性冲突等因素,所以不是真正的悲剧,其主要理论依据即是雷德的悲剧理论。
在从悲剧美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真正的悲剧之后,钱锺书又从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命运观这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国缺少悲剧的道德与哲学根源。他认为,白璧德在《卢梭和浪漫主义》一书中把中国缺少悲剧这一事实归因于中国人缺乏“伦理的真诚”(ethical seriousness) ,还不够有说服力,事实上,“中国式的对美德的等级安排”(peculiar arrangement of virtues in a hierarchy)才是导致中国缺乏悲剧的道德根源。在这种等级制的道德体系中,每一种道德价值均在道德谱系中被规定好了自身的位置,且所有伦理要素和权利诉求均按照严格的“价值秩序”(order of merit)予以框定。这就导致不同等级的伦理要素之间的冲突被极大地弱化,因为,既然道德的价值有高低之分,则低等的价值必然免不了失败的结局。然而,由于被忽视的低等伦理要素会因为高等伦理要素的充分实现而得到弥补,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悲剧性过度”(tragic excess)。钱锺书指出,《孟子·离娄》篇中关于“大人”品行的警句及柳宗元的名篇《四维论》都可以证明道德等级制的存在。
[欧文·白璧德(1865-1933)]
在《孟子·离娄下》,孟子论“大人”的品行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7]在《四维论》中,柳宗元论廉、耻这两种美德与义的关系说,“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8]按照孟子的观点,信低于义,按照柳宗元的观点,廉、耻只是义的小节,也比义低一等,这两种观点确实证明了道德等级制的存在。按照钱锺书的看法,道德等级制弱化了不同美德之间的冲突,也就弱化了道德取舍的复杂性与诸如舍生取义、忠孝不能两全之类抉择的悲剧性。
钱锺书又从命运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缺少悲剧的哲学根源。他指出,中国人一向被视为宿命论者。但奇怪的是,中国古代剧作家却很少以命运作为“悲剧的动机”(tragic motif)。他进而指出,“悲剧性命运”(tragic Fate)和“宿命论”(fatalism)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宿命论本质上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和被动接受的态度,其结果是无生气和无所作为。而“悲剧反讽”(tragic irony)主要体现在当人面对命运的一再作弄时,始终不放弃抗争的努力。他又指出,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命运与希腊悲剧中所揭示的命运存在着截然的差异。为了说明这种差异,他引用了英裔美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和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的如下观点:“当今那些怀着科学梦想的朝圣者们就是古代爱琴海地区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对冷漠不知愧悔且将悲剧事件导向必然结局的命运的认识,正和科学的认识相重合……自然的法则就是命运的法则。”[9]钱锺书认为,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具有古希腊悲剧家的命运观中所蕴含的“科学的力量”(scientific vigour),而是彰显了“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他介绍说,布莱得雷博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一书中严格区分了“诗性正义”与“悲剧性不义”(tragic injustice),而布莱得雷所谓“诗性正义”,是指幸运和厄运按照当事人的功业按比例加以分配。钱锺书指出,中国人对命运的认识更接近于论功行赏而非推因知果。它不是价值中立化的自作自受的观念,而是一种“情感化的信仰”:美德是自身的奖赏,而且还会有追加的奖赏。它不仅仅意味着“种豆得豆”(as you sow, so you reap);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快乐的种子不可能结出苦果”(as you sow in joy, you cannot reap in tears)。不过,因果关系是成正比的,而行为和奖赏却未必成正比。中国人通常辩解说:我们或者在过去已得到报偿,或者在未来将得到补偿。钱锺书认为,这一观念与古希腊的观念正好相反。
综上所述,钱锺书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既援引瑞恰慈、雷德、布莱德雷等西方学者的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德莱顿的悲剧作品从理论阐发与文本对照分析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的严肃戏曲为何不是悲剧,又从中国人的价值观、命运观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缺少悲剧的原因,并非像他自谦的那样,仅仅“从剧本自身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之所以没有悲剧的原因”。他总结该文的价值说:
首先,它驱散了甚至包括中国批评家在内的对中国古典戏曲的错觉。其次,它有助于比较文学修习者恰如其分地看待中国戏曲在艺术殿堂中的位置。我一向认为,比较文学的修习者如果能将中国古典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他们将会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这有可能会使他们对西方批评家确立的批评教条(dogmata critica)加以重大修正。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的修习者来说,就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只有借此才能知道中国古代批评家所面对的研究资料不同于西方批评家所面对的研究资料,也才能明白西方文学批评的那些首要原理为何未被中国批评家采用,反之亦然。这是我在多方面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贯目标。为了充实我们的某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走向外国文学;为了充实我们的另一些审美经验,我们必须回归自身。文学研究中的妄自菲薄固然不可取,拒绝接受外文明成果的爱国主义就更不可取。这段方法论性质的学术自述,同时为比较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可与本书第三章“作为中国文学优越论对立面的‘比较文学’论”一节相对照。钱锺书主张,中国的比较文学者应该将中国古典文学纳入研究视野,藉以修正西方批评家确立的批评教条(dogmata critica);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应该采纳比较文学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文学作品,认清中西方文学批评观念与原则的不同审美经验来源。此外,《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还用很大篇幅反驳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元则有悲剧在其中”以及《窦娥冤》、《赵氏孤儿》为世界悲剧经典的论断。笔者将另文探讨。
注释:
[1] 钱锺书:《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载《钱锺书英文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译文见附录,为笔者所译。此后凡征引该文处,概不出注,谨此说明。
[2]见《天下月刊》( T’ien Hsia Monthly)1935年8月号,43页;《钱锺书英文文集》收入此文时,对此并未修订,见该书61页。
[3] Louis Arnaud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pp. 344-345,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4.
[4] Louis Arnaud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p. 348,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4.
[5] Louis Arnaud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p. 353,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4.
[6] Louis Arnaud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p. 346,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4.
[7]杨伯峻:《孟子译注》,1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8]柳宗元:《四维论》,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 128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9] Louis Arnaud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pp. 353-354,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4.
本文系龚刚著《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增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第五章第二节,略有改动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