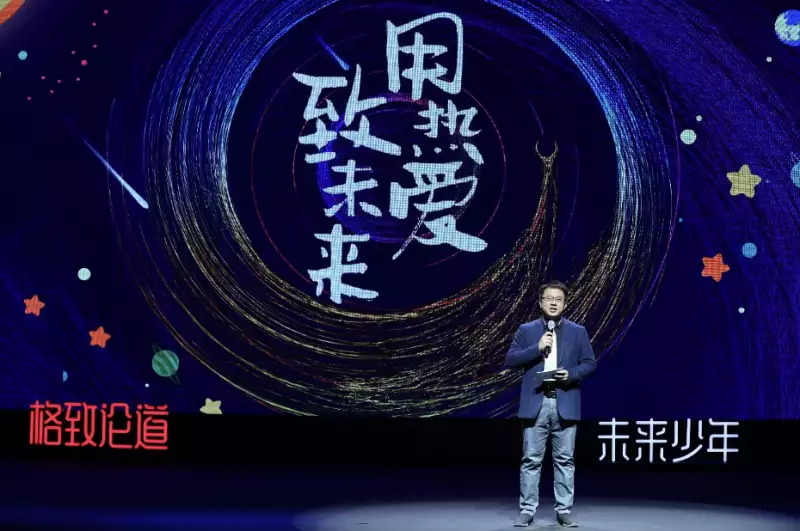今年最痛的热搜,她消失了
每年的8月15日,我们都无法轻易翻篇。
因为77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个痛苦的时间,刻在了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无法轻易抹去。
但刚刚过去的昨天,我们也同样不该忘记。
2022年8月14日,是第10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为什么是第10个?
说来残忍且令人心痛。
1931年~1945年间,20多万中国女性被迫沦为性奴隶,“慰安妇”成为强加给她们的称号。
但这群女性的伤痛,直到2012年才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导演郭柯去往广西,三次拜访了当时92岁高龄的农妇韦绍兰,并拍摄了纪录片。
取名《三十二》,因为截止到那时,登记在册的仍在世“慰安妇”的数量只有32人。
直到这时,这些尘封的故事,才算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中。
2017年,同系列纪录片《二十二》在多轮众筹之下得以公映。
图源:豆瓣
因为拍摄当时,登记在册的仍在世“慰安妇”的数量,只有22人。
等到影片上映,很多阿婆已不在人世。
到2018年,《二十二》中的阿婆仅剩6位在世。
到了今年,人数似乎缩减到只剩2位。
影片中的阿婆在逐渐离开。
但影片之外,又陆续有新的受害者站了出来。
据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文章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在世人数仅为12人。
看到这样的数字变化,她姐一时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因为数字增加和减少,都是伤痛。
22、12、2……
这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带着痛苦的记忆走到今天的、活生生的人。
而她们,至今仍未等到道歉。
只要一天没等到道歉,她们的故事就一天不能被忘记。
从哪讲起呢?
不如,先从阿婆韦绍兰说起。
图源:豆瓣
注:由于在这一议题下,“慰安妇”较“性暴力受害者”更广为人知,文中仍暂时使用“慰安妇”一词。
“只愁命短不愁穷”
韦绍兰,总是佝偻着腰背,沉默地穿行于山涧、田野、小桥边......
图源:《三十二》
郭柯来拍摄时,她已92岁。
韦绍兰和常见的阿婆没什么不同——着装朴素、满头银丝、面孔上有着风吹日晒的操劳痕迹。
只是日子更加难一些。
她挖了一生草药,如今年岁大了,只能指望着新坪乡发放的每月90元,按季度领的低保费。
为了节省开支,韦绍兰自己洗衣做饭、提水拾柴......
图源:豆瓣
吃食也只买最便宜的白菜,“一次买五块钱的,也可以吃很久”。
图源:《三十二》
就这样,她守着砖土房,和六十多岁的儿子罗善学相依为命。
有时唱起山歌,“只愁命短不愁穷”,还能宽慰起旁人。
图源:《三十二》
这是她儿时从隔壁村的十二爹那学来的山歌。
每次十二爹来放牛,韦绍兰和一群男孩女孩都会团团围住他,嚷着闹着要学山歌。
那时她嗓音清亮,歌声飘过九重山。
图源:《三十二》
但我们都知道,韦绍兰和旁的阿婆是有不同的。
她的岁月里除了青涩的美好,还有一段磨砺着沙土,硌得人心里疼。
图源:《三十二》
那是被扣上“慰安妇”名头的一段过往。
1944年,24岁,新婚不久的韦绍兰,被闯入桂林的日军发现了。
那时炮火伴着掠夺,日军在亚洲各个邻国共抢掠侵犯了40万女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受害者高达20万人,韦绍兰就是其中之一。
明晃晃的刺刀举起,让人恐惧得不敢出声、不敢落泪。
图源:《三十二》
这把刀没捅进血肉,只是挑断了她背着女儿的背带。
不满一岁的女儿掉到地上,韦绍兰无法逃跑,连带着女儿一起被日军掳走了。
一路上,一个又一个如韦绍兰一般的女子接连被日军拖到车上,运往附近的据点。
那是一个离新坪乡30公里以外的炮楼。
韦绍兰在这里熬过了近一百个日日夜夜。
是监禁,更像圈养。
强奸不论时间,有时来一个人,有时三五成群。
图源:《三十二》
为了让圈禁的妇女听话,日军发明了种种规矩和酷刑。
“服务不能令官兵满意的,鞭打;
在服务时哭泣的、不按官兵要求去做的,鞭打;
身体有病的,隔离或者处死;
有逃跑想法和行为的,鞭打、断食,情况严重的处死。”
还有一种折辱叫“四角牛”。
日军把逃跑的女性抓回来后,让她们保持手脚撑在地上的姿势,腹下方还立着一柄尖刀。
动作不标准会被鞭子抽打,时间长坚持不住就只能眼睁睁被利刃洞穿。
图源:网络
但仍有许多人想要逃,韦绍兰也不例外。
被抓来的女性还要替日军洗衣、做活,韦绍兰便常常在洗衣时观察地形。
一天,士兵打了盹,韦绍兰抱起孩子迈过熟睡的日军,逃了出来。
图源:《三十二》
大道不敢走,只能挑小路。
30多公里土路,全靠步行。
她走了几天几夜,最终回到了家。
但一切回不去了。
丈夫看到她第一句话是,“出去学坏了”“还知道回来”。
图源:《三十二》
韦绍兰一听,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
婆婆和邻里说:“她不是学坏了,是被日军掳了去了。”
图源:《三十二》
丈夫自然知道那不是学坏,韦绍兰也知道丈夫的知道。
但她也明了丈夫的言下之意:“哪个男人会瞧得起这样的女人呢?”
图源:《三十二》
日军的折磨没有让她求死,回到家后韦绍兰却饮了农药。
但没死成,她被邻居救了回来。
只是,心早已如死灰。
女儿因营养不良去世,她又发现自己怀了日军的孩子。
婆婆劝她把孩子生下吧,因为被日军折磨过,这个孩子不要可能就再也怀不上了。
图源:《三十二》
1945年,韦绍兰诞下罗善学。
一个月后,日军投降了。
但苦难并没有到此结束。
韦绍兰没上过学,那时“只有男官,哪有女县”。
因为家穷,罗善学也没有念几年书,就“看牛”了。
小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韦绍兰和丈夫自己捡野东西吃,把粥留给儿子,艰难地将他养大;
图源:《三十二》
最难的,还不是穷。
而是始终萦绕在他们一家身上的异样眼光。
罗善学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但走出家门,就连小孩都敢围着他大喊取笑:“日本人,日本人。”
图源:《三十二》
出门尚且被歧视,更别提组建家庭。
十里八村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六次相亲,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
“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不要名誉了么?”
罗善学一生和母亲相依为命,也是愁。
等韦绍兰离去了,又有谁来陪他说说话,帮他倒杯水呢?
但韦绍兰比儿子想得开,她总说: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图源:《三十二》
2019年,韦绍兰在雾霭青绿的九重山间去世了。
身后只有一间土房,几张桌椅,和无所依凭的罗善学。
“幸存者”
有人说,她们是“幸存者”。
因为被掳走的很多人被强暴致死,染上病的,被活埋,怀了孕的,被剖腹杀害。
而她们,毕竟捡回了一条命。
但细数起她们的经历,她姐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幸运”二字的。
像韦绍兰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
每个人的故事讲起来,都痛到让人不忍听下去。
这位老人叫陈亚扁。
被日军掳走的时候只有14岁,被折辱了整整四年。
四年后抗战胜利,陈亚扁活了下来。
但人生却像走到了头。
村里的人容不下她,像恨日本人一样恨她。
她只能躲进山里,过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才被政府救出来。
她的子宫被折磨得严重变形,后来8次怀孕,不是流产就是死胎。
有人叫好,说这是她给日本人睡觉的报应。
有人骂她日本汉奸,说是上天对她的惩罚。
“日本妓”“日本婆”,这些外号戳了她大半辈子脊梁骨。
要说她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幸运,除了等到抗战胜利,大概就是遇见后来的丈夫了。
丈夫不惜花尽半生积蓄,陪着她四处寻医问药。
他告诉陈亚扁:
“就算我们不能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过也是一个家。”
第九次怀孕,她终于平安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婴。
陈亚扁老人和孙女合影
多年以后,前去探访的记者看见陈亚扁和孙女聊天的场景,不忍心再去提及当年事。
她的面容洋溢着幸福,生活已经看不见痛苦和屈辱。
冬去春来,岁月萧萧,如果时间真的能掩埋掉所有残忍,该有多好。
可残疾老废的身体,和长久的精神折磨,仍时时提醒着她们伤痛从未远去。
在同村人的印象里,林爱兰是个“沉默孤僻,令人琢磨不透的老太太”。
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叫她“阿黄”。
阿黄曾是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
老人比划起当年子弹上膛开枪的样子,动作爽利,目光炯炯。
她的眼睛黑亮亮的,鼻子微挺,有着精巧的圆脸,年轻的时候想必可爱又灵动。
但在战乱年代,这样的长相给她带来了不少“劫难”。
阿黄性格刚硬,被抓后死死拽着裤腰,结果大腿被生生戳穿,疼晕了过去。
抓住机会逃跑后,日本兵便找到她家里,当着她的面把她的妈妈捆住手脚扔进了河里。
阿黄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可每每讲到母亲,总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哀戚,哭着说是她自己害了母亲。
几十年来,身体的病痛在一点点侵蚀着她。
和大多数“慰安妇”一样,她没有了生育能力,被打过的地方总是突突地痛。
被戳穿的大腿早已坏了筋骨,她只能终日坐在椅子上,双手支撑着椅子,摇摇晃晃地挪动。
阿黄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刀。
菜刀、水果刀、镰刀……
放在床上、桌子上、地上,最容易拿到的位置。
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操起镰刀随时准备着。
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老人也一样,手里始终紧紧握着一把刀。
吃饭睡觉,都离不开这把刀。
床边放着一块磨刀石,没事的时候,她总是反反复复地磨刀。
一遍又一遍,总觉得刀不够锋利。
没有人能真正从暴行中走出来,她们只是活了下来。
老人们去日本上诉的时候,遇到前来帮助的日本律师。
有的老人一听到日本男人讲话,就抑制不住地颤抖。
她们害怕啊。
大半辈子过去了,少时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彼时的痛和惧却久久地延续着。
一不留神就会钻进她们的梦里,掀起一夜风雨。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夜晚被梦魇囚困,白天又要被白眼淹没。
在当时很多人眼中,和日军行苟且之事,不配做受害者。
没能打死日本人,更是称不上英雄。
可是村民忘了,家人的性命、全村人的性命,都是日军要挟她们的价码。
她们明明应当是堂堂正正的英雄啊,却成了过街老鼠。
于是这段血淋淋的过去,在这么多人的肚子里烂了几十年,连同当年身体残留的病灶一起成了坏进骨头里的旧疾。
她们哪里是什么幸存者。
无关幸运,只是存活。
三十二,二十二,十二......
从地狱里趟过,她们明明已经不怕死,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力地活。
张先兔住的房子破败,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日子嘛,就要打点整齐些,我喜欢体体面面的,一辈子都是。”
图源:新华社记者 范敏达
韦绍兰爱唱歌,她唱:
“天上下雨路又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
自流眼泪自抹干。”
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这世界红红火火,会想死吗,没想的。”
韦绍兰
这么多年,她们用沉默代替控诉,放任时间把记忆碾碎磨平,埋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
曹黑毛老人拍照的时候,笑容可掬的样子像是一只可爱的树懒。
曹黑毛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聚在一起,冲着镜头比划剪刀手。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
王玉开看到80岁日本军官的照片,没有哭也没有怒,反而打趣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图源:王玉开和常去探望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合影
记忆可以变得模糊,仇恨也可以淡去,只是看淡并不等于释然,彻骨的伤口始终都在那里。
直到人们找到她们,她们才知道,原来是可以起诉的。
从1995年开始,一些老人陆续向日本政府起诉。
为了指证日军犯下的罪行,她们去到当年被关进去施暴的窑洞炮楼里,把烂进骨髓的记忆重新扒开,给世人看,给自己看。
法庭上,老人们晕倒了也要坚持诉说,说到悲从中来,哭得撕心裂肺。
万爱花
从来都不是过去了,只是无可奈何的“算了”。
一旦开了这个头,谁也不愿意再算了。
法庭上,要求展示当年日军专门针对慰安妇的刑罚“四脚牛”。
满头白发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趴在地上,拱起腰背演示,所有人都不忍再看。
不能就这么算了。
然而在不争的事实面前,日本仍保持着“不承认”的姿态,阻挠菲律宾及各地区和国家“慰安妇”纪念雕像落地,污蔑被抢掠欺骗的妇女是“自愿卖淫”......
在日本辞典《广辞苑》中说,“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军官的女人”。
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驳回诉讼。
最后认定了侵害的事实,却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其败诉。
日本试图否定历史。
而我们呢?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遗忘历史。
2016年,上海上海计划拆除海乃家——日军“慰安所”旧址。
邻里四方赞同拆除,委婉地说这段耻辱该过去了,话锋绕来绕去还是亮出了“耻辱感”的来由:“慰安妇不就是妓女吗?”
图源:网络
有人说“这段历史不光彩”。
有人说“慰安妇的事情不正能量”。
图源:《三十二》
看到这样的言论,她姐感到痛心。
很多人只是沉缅于构建出来的历史伤痛中,却不敢真实地向那些亲历者望一眼。
“慰安妇”,到底是什么?
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意思是随行慰劳军人的妇女,是为了美化当年的强抢行为而裹上的一层糖衣。
在中国,这些女子大多是像韦绍兰一样被强抢去的。
她们是被迫成为“慰安妇”的。
她们是“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更是战争性暴行下的受害者。
对“慰安妇”受害者们的污名化,无疑是掷向她们更为锋利的刀刃。
图源:《三十二》
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上诉,一次又一次地败诉。
只是,她们终究是跑不过时间的。
王玉开,2013年12月31日离世。
张先兔,2015年11月12日离世。
林爱兰,2015年12月23日离世。
陈亚扁,2017年5月11日离世。
韦绍兰,2019年5月5日离世。
今年,陆续有4位老人离世。
······
当年那些起诉日本政府的老人,如今已经带着无尽的遗憾长眠地下。
她们要的多吗?
她们想要的,只是一个真诚的道歉。
只是,至死也没有等来。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也不多。
只有不淡忘、不扭曲这段暴行,不再将污名附着于她们之身。
尽力去记录,去奔走呼号,不让这些未结的话语成为过去。
点个「在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她刊
图源:《1984》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
上一篇:一个16岁的女孩被日军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