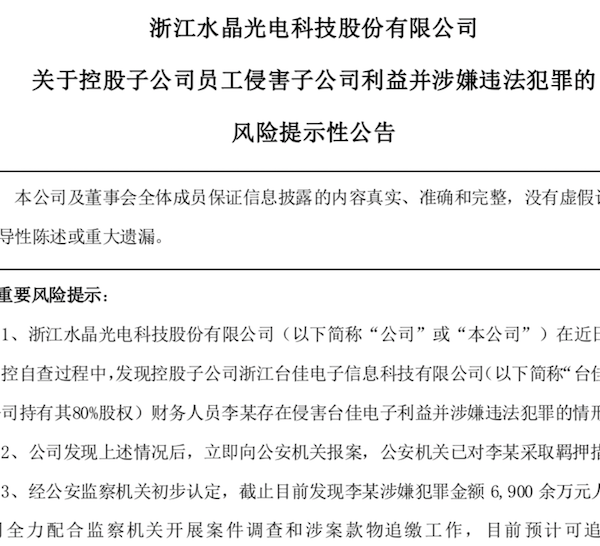“公正”为何成了自私的遮羞布?
文 | 李厚辰
我们对“公正”决不陌生,它填充了几乎所有公共争议。不论是骂方方的、维护方方的,支持死刑的、反对死刑的,支持建制的、反对建制的,这些出发点(至少是自己认为)都是为了公共福祉。
我们都觉得人们“自私自利”,但想想网络争议,我想为利益的可能少,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善恶”。
且论辩双方没人为“恶”辩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认为的才是“真善”。这样的争论,从“真爱国”、“真民主”、“真环保”到污蔑对方的“田园XX”不一而足。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敏感于“善恶”并因“善恶”而发言的时代,为何不呈现为真理越来越分明,“善”被更好地维护,而是相反呢?
《圣经》创世记中有个令人费解的细节,神不希望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食用的“禁果”不是什么“罪恶之果”。相反,是“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因智慧得以分辨善恶,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件坏事,而是件好事。神为何要禁止人因智慧而分辨善恶?
也许回看网络上人们“因智慧而分辨善恶”,因而生发出的这么多争论攻伐,我们就该理解一些了吧。
01.
“公正”致恶
“公正”和“正义”当然是一个算计的问题,其中包括“质”的算计,例如杀人抵命,例如方方争议中“诋毁之恶”的传递性;也包括“量”的算计,例如原子弹与战争伤亡,例如碳排放。
这一切的算计,自然是因为善恶公正。
1943年,若依靠普通战争手段拿下日本,美军可能要损失至少一百万人,而日本也将死亡更多军人和平民,且每日持续的战争都在夺去更多人的性命。两颗原子弹下去,二十四万人死亡,换得日本次日投降。二百万比二十四万,这难道不是小恶对大善?
就前两日,胡锡进还在鼓吹中国应该拥有更多核武器。这里也很简单,美国拥有大概5113枚核弹头,俄罗斯拥有4800余枚核弹头,而我们拥有不超过500枚。5000与500的对比,核扩军有什么“善恶灰色地带”?
反环保共识也是一样,所有国际碳排放方案都明显不公平,按照这些方案设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2.3-6.7倍的人均碳排放权利。凭什么过去造成了更多环境问题的发达国家,竟然还拥有更高的人均权利?这些国际方案反正都是“恶”的,又为什么需要去参与?
兴许上述观点,你都还很认可。也很难说里面有什么“不够客观”之处。
如果去了解二战前德国的历史呢?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13%国土,12%人口,因为严重的战争赔款而民不聊生。且一战失败几乎可以说是外被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等不争气的盟友拖累,内被魏玛民主派,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拖累。面对“不平等条约”《凡尔赛条约》,德意志人报复犹太人并为“公义”与“德国国格”进行补偿性的侵略波兰和法国,又有何不可呢?
这与今日之民族主义观点何其类似?我当然明白,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决不可能依靠论证其是“假正义”,我们相信的才是“真正义”予以回应的。
在对公正量质算计后,这些都是极其“有理”的善恶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以死抵死”的死刑之正义;认可“污蔑传递”的“方方有罪”之逻辑的正义;认可“原子弹”终止战胜的正义;认可商业是社会真正“善之动力”的正义;认可大国应该拥有对等的核力量,全球人应该拥有对等的“人均碳排放”之正义。
那么纳粹德国的“复兴大业”同样可以获得“正义性捍卫”。
用智慧分辨“善恶”,尤其是评价“公正”和“平等”,会让我们做出极其可怕的事,但又觉得无比正当。公正就会在这些地方,转向对“恶”的支持。
02.
六种公正致恶的逻辑
这不是一篇抒情散文,我还是要具体地说明,“公正”到底是如何导向可怕“恶行”的。
(1)小恶的合理性
读者们都听过一个笑谈,就是流氓当街挑起争执,极尽恶心下作之行,对方一直忍让,但实在忍无可忍,低声粗口骂娘。流氓立马抓住这点,指责对方竟然“侮辱自己的母亲”,罪无可恕。
我想这不是笑谈,在日常实际争执中,若一方忍无可忍动手,对方一般都会立即大喊“他打人!”“他竟然打人了!”,从此之后善恶逆转。
故事虽然可恨但极具合理性,这些情形发生时,还真会得到旁观者们的支持。
恰恰在于“公正”的善恶算计中,有因果性的“小恶”面对“大恶”确实是可以取得合理性的。且不管时间在前,还是在后。
若网上有人用很恶毒的语言侮辱我,我回骂两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公正的回击”。甚至我先浅浅侮辱对方,引来对方极其恶毒强烈的侮辱我,只要对我伤害够大,似乎最开始我那个“浅浅的侮辱”也变得合理起来了,甚至得到了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证明。
在网络争论乃至现实争论中,靠点出和强调对方的“大错”,来合理化自己的“伤害”,是绝对屡试不爽的方式。有多少伤害借此得到了辩护?这就是“公正”的逻辑。
(2)报复为善
你厌恶“网络人肉”吗?我想可能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公正”的逻辑之下,当一个人带来了伤害,如果他本人不受到报复,岂不是“很不公平”。在这个情况下,有法必究,对他造成伤害甚至成为一种“义务”。
这当然是一切“网络义警”背后的合理化逻辑,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至少大家达成了一种“报复为善”的共识。
对于我们支持的人,这是一种“网络暴力”,对于我们讨厌的人,那就是一种“网络公正”。当我们谴责“网络暴力”的时候,是要专注其“暴力性”,还是要专注其“诽谤性”?
我们经常更加关注后者,问题并不出在“暴力”,而是这种暴力是“诽谤的”。言下之意,只要不是“诽谤”,网络暴力就是合理的报复。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能达成“何谓诽谤”的共识吗?
(3)善恶必然教条化
还记得每有品牌“辱华”之时,明星们争先恐后地与品牌解约么?甚至晚解约的都会因为不积极而受到谴责。或是在庆贺之时,明星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忠心,未表达的被网友们制作成名单“游街示众”。
我们总是抱怨有时“不大声赞扬”甚至都是一种罪过,有没有想过为何善恶成了对于“行为”的教条式要求呢?
因为我们在考虑“公正”问题,尤其是显性公正时,例如“爱国”。在人们各自的心里有多么“爱国”,这自然难以衡量和计算。能够计算的,是为了“爱国”,相应的代价你是不是承担了,该发的言是不是发了?该舍弃的利益是不是舍弃了?
我们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因为算计和评估的必要,必然成为一种行为和言语上的教条。
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共担风险,共负义务,并据此达到一种“平等”。
因为我们要阻断一切人以“他们内心怀有善”作为辩解的空间。这就是你的朋友圈里大家都转发了什么内容,你被迫转发的缘由,“转发为善”在这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教条。
(4)教条善压制实然善
善恶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西方,主要呈现为“政治正确”,即一套平等的,人人都需要遵守的教条,对一切例外的不宽容。
在我们这里,我想主要呈现为“负能量”的教条和“道德自律”的教条。“负能量”上篇文章已经说过,在这里不做重复。
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指责(实际上不可能),我们还达成了“道德是自律,而非他律”的平等教条,意思是只要不触犯法律,谁都不要用“道德”指责他人。
不管背后是否有实际的“善”或“价值”,每个人都要免疫被他人“道德评价”的处境。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主张,可以说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极端形式。是“善恶共识”不可能达成条件下的终极“善恶算计”。
你就会发现,“公共善”要么极端后退为“绝对都不可做”的消极教条,要么极端前进为“必须大家都一起做”的积极教条。都符合某种“公正”的形式原则。而真正的善,就在这两种教条中被狠狠地压抑。
(5)先天禀赋为罪
比起仇富,我们更仇视“富二代”。一个人若做了些什么获得财富,哪怕他做的事情是不那么合乎市场伦理,有时都会被当作一种本事。但什么都不做就靠家庭而获得“财富”,才让人恨得牙痒痒。
说明,比起实质的恶(不合乎市场伦理),我们更讨厌“不公平(继承清白的财富)”。这当然不仅仅只在财富的领域。
在PUA技术构建男性“以恶追求”的必要性时,外貌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成为了“原罪”,那么PUA就是外貌和财富都不具备先天禀赋男性的“必要之恶”,是一种合理的补偿。
在《观察者网》抹黑方方时,她来自“大知识分子”家庭已经不是一个优势,而是一种“原罪”了。先天占有更多资源,或先天拥有了一些禀赋,因为其“不平等”,甚至是一种“错误”,并导致对先天禀赋的抵制和憎恨,这在当今的平民主义文化下,绝不是一件新鲜事。
公正的敏感,让自然差异甚至都带有罪过。
(6)矫正正义不可能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期,曾颁布《平权法案》,其中有给予非裔和拉丁裔在美国升学中的配额制度。这种矫正正义成为对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华裔的实质性“歧视”。在川普任期内,遭到了巨大的抵制。
在我们这里也一样,2016年,两部委推出高考招生调整,从12个省份调出相应名额,补贴给其他各个省份,其中江苏省和湖北省调出名额最多,分别调出38000个和40000个,就引发了主要是这两省的极大抵制。
从某种绝对“平等”和“公正”的观点来看,任何“矫正正义”都是对“非矫正对象”的歧视,尤其是在实际执行中,“矫正成本”一般不可能在“非矫正对象”中绝对公平的分担,那这样在某种善恶算计的意义上,当然是明显“不公正的”。
以上六点,分开来看每一个,都是“公正”而“正当”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在某种“善恶算计”的基础上构成其合理性的捍卫。
但当这六种倾向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解释我们社会中和网络上面对的一切乱象。
一个人人都“知善恶”,“敏感于公正”,凭借公正名义而言行的社会,合在一起竟然丝毫不是光明和积极的,而是险恶阴暗的。
据此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道德滑坡”的社会,我并未看到公共言论环境被“自私”和“冷漠”的言论占据,反而公共言论中言必称善恶公正,今日之乱象是借“公正”之名。
03.
告别“公正”为公共善的时代
所以我是要主张一种“去善恶”的环境吗?大家多谈“利益”和“实际”,少谈道德和善恶?
绝不是。我要绝对反对的是一种以“公正”作为公共善核心的环境。人们总想说“XX啊,多少恶事假汝之名而行。”这个“XX”,原话是“自由”,有时被化用为“爱国”,有时是“民主”,有时干脆是“道德”。
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其实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临刑时也应该说出我今天所看到的问题。“公正啊,多少恶事假汝之名而行。”因为大革命的基础价值即“平等”,是一种追求激进“公正”的尝试。
对于公正(equality)的算计,以“正义”之名,让自私甚至都变得不再自私,让暴力不再暴力,让伤害正当,让“小恶”得到捍卫,让“行为教条”被人自觉遵循维护。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维护任何“不公正”,不管是财富收入,还是任何的资源分配。社会整体财富分化缩减,资源更加平均分配,都是非常可欲的结局,可以作为衡量社会整体善恶的标尺。
但公正绝对不是衡量行为善恶的唯一方法,摆脱看上去无懈可击的道理,尤其是再明显不过的数字,接受一种“差异政治”,这是个严肃而永恒的话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意识到绝对公正之不可能,城邦中的“统治者”、“辅助者”与“一般公民”的分工必然性,平等之不可能,因此只能依靠“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来作为此种不公正的调和。
说到底,“公正”是一种“自利的合理化”,且既可以用于弱者诉求利益,也可用于强者拒绝放弃利益(矫正正义成本未公平承担)。因此即便对于“弱者”,公正作为善恶算计也是一件坏事。
要我说,“公正”已经成为了自私的遮羞布。
04.
“公正”最好仅仅自律
当然“公正”作为公共善的核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尤其对于我们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一套从分配不公出发的善恶观;而我们的近代史被描绘为被“不公对待”的屈辱历史,里面充满着报复的因子;战后的公共秩序又被描述为以“多元”和“公正”作为核心的秩序;而改革开放后明显的分配差距更加剧了显性的“不公”。
这四股力量交织在一起,教育和塑造了强烈的“公正敏感”的社会文化,也让上述六个公正的必然问题凸显出来。
尤其当我们缺乏其他实质性的“善恶”共识,公正就额外会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替代品。就像夫妻间情感的实质丧失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公正”就成为了维系关系的方式。
除了“公正”,善恶当然会呈现为很多其他的形式,不管是儒家的“仁”,西方的“爱”。纵观各个美德充盈的人物,他们或许关注他人之“公正”,但甚少关心自己是否被“公正”对待;奖励是否充足,或是厄运承担是否太多。
一个民族也一样,他们可以关注天下的“正义”,只是不必每次这样的关切都七拐八拐的回到对于他们自己是否被“公正对待”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一种公共道德的虚伪:一旦问题关乎“公正(即实际利益)”,大家群情激愤,正义喊声震天。
当道德呈现为“真诚”、“奉献”、“宽恕”之时,人们要么摆出老练的嘴脸斥责这些“乌托邦”,要么摆出嫌恶的嘴脸,斥责这些是“道德绑架”。这些玩意儿最好都拿来自律,能够他律的唯有“公正”。
只关注他人之公正,而非自己的。我倒觉得人们刚好说反了——“公正”最好仅仅自律。其他的“道德”,那些才是我们需要用来“他律”的善恶准则。
如果要选一个开始的话,不如就从我上次说的“真诚”开始吧。
尾声.
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正是自己的恶习
这不是个好接受的结论,因为“公正”看上去天经地义,受到“公正”加持的“自利”,都变得无可指摘。
但我们恰恰应该看到“公正诉求”的“自利底色”,并回忆我们的经历中,“公正”在多少次被当作恶念与恶行的捍卫,成为教条,成为一种过度精巧的算计。
我想正是看到人身上这种“公正”的敏感和天性,这种必然算计的“智慧”,伊甸园中才会有“善恶树智慧果”的禁令吧。
确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报复,大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相残,再到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报复——谁都认为自己因“公正”而“正义”。“公正”追求,这种“善恶智慧”已然成为诅咒。
这让我一再想起哈维尔在1990年的致辞,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初获自由,正是应该大谈“公正”以清算过去之时,但他说:
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
查看更多往期内容
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李想主义」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