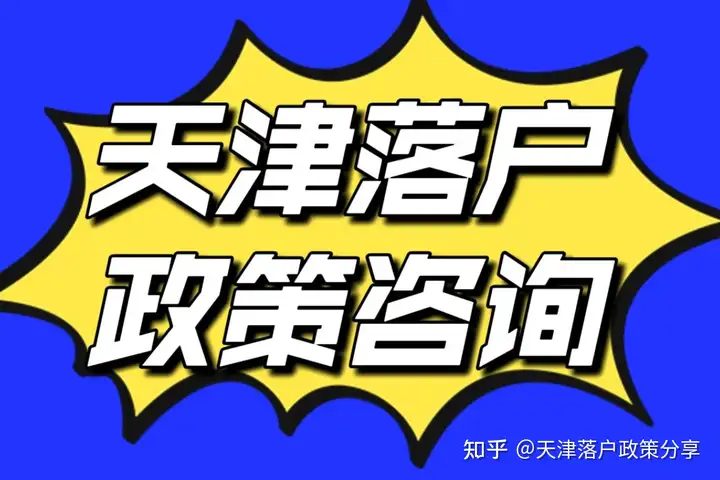官邸失窃之谜
这几日,穆木修老有种预兆不祥的感觉,左眼皮动不动就跳,“噗、 噗……”像发了酵的粪坑里鼓出的气泡,毒太阳一蒸,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没个消停。
“左灾右财”,老话都这么说。
“哼,老子出生入死十几年,还信他娘的这一套不成!”穆木修很想这样粗鲁地骂一句,来表示自己内心的轻蔑和不落俗套。可惜,骂虽然是骂了,俗套仍然像张网似的难以摆脱。
1946年1月4日的这个上午,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细碎的阳光乱针 似的扎透绛紫色的窗帘缝隙,刺进穆木修这间朝南的公寓卧室。时针已指向上午10时,新上任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调查室主任仍然像个懒婆娘似的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厚重的橡木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幽灵似的闪进一个身影。正因左眼皮乱跳而心绪不宁的穆木修吓得浑身一激凌,猛然侧身,反手攥住了卧枕下的手枪柄。
进来的是安南籍的女佣黎。
穆木修抽回抓枪的手,愤愤地骂道:“娘卖×的,走路像贼一样,吓老子一跳。”
女佣瞪着一双幽邃的黑眼珠,红唇半启,“啊啊”地不明就里。安南女佣不懂中国话,她是依惯例来给穆木修送早点和报纸的。
这女人虽然不懂中国话,年纪看上去也不小了,可长得还颇有几分姿色。一张浅棕色的圆脸上嵌着一双凹陷的黑眼珠,两道飞扬的柳眉直插双鬓,虽说颧骨高了点,嘴巴大了点,可组合得别致有味,透出一股来自东南亚的异域风韵。就因为这,半个月前总务部门把她从职业介绍所领来,穆木修一眼就相中了。
女佣扭动着腰肢走到床头柜前,依次放下报纸和咖啡。这女人煮得一手好咖啡,据说她原来在老家河内就在法国人家里帮佣,擅长西点西饮,后来主子调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也把她一铺盖卷来了中 国。抗战时期汪伪收复租界,法国佬顿作鸟兽散,这女人从此沦落上海街头,靠给人帮佣为生。
当然,这些背景材料都是总务部门从职业介绍所道听途说来的,鬼晓得是否属实。
黎放下咖啡和报纸,细腰一扭,转身欲走,恰好把两爿颤颤微微的肥臀扭向了斜倚在床头的穆木修。新任市党部党务调查室主任顿感耳热心跳,一股邪火忽地蹿上心头,未及多思,便鬼使神差地伸出了爪 子,在那砣丰厚的肉堆上狠狠地掐了一把。
黎“哇”的一声怪叫,仿佛中弹一般,反应煞是敏捷地跳将起来,手里的托盘顺势朝身后扫去。幸亏穆木修是受过特种训练的正宗货,反应亦属不差,眼明手快地一把攥住对方的手腕,轻轻朝怀里一带。黎顿时失却重心,脚步趔趄,“扑通”一声栽在床沿上。
黎大概是摔重了,脸埋在被褥里一动不动。“嗨,装什么蒜呢?”穆木修搡了搡她。黎这才哼哼唧唧地支起半边身子,可没等撑直,又“啊 呀”一声趴下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这一趴恰好趴在穆木修的怀里,两跎绵软的胸脯肉结结实实地压在了穆木修的大腿上。
“哎哟哟……乖乖……”穆木修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嗖嗖”地从大腿根 处辐射出来。他趁机又掐又摸。两人就这么近乎“搏斗”似的嬉闹了好一会儿,黎才蓬松着一头茅草似的乱发,逃出了穆木修的“魔掌”。
望着黎的背影,穆木修乐不可支地发出一阵傻笑:“呵呵,嘿嘿、嘿……”烦乱的心绪觉得平复了许多,浑身的脉管根根贲张,血液流得畅快而又滋润。他拿起新到的《申报》,心不在焉地浏览起来,边看,边腾出一只手,端起床头柜上的咖啡杯,送到嘴边,目光却被报上的一条新闻牵了过去:
【本报讯】据市警察局常熟路分局最新通报,昨日午夜时分,本市太原路87号的一幢私人住宅遭宵小光顾。窃贼撬开矮墙外竹篱笆门上的铜锁潜入院内,又打碎玻璃逾窗进屋,将值钱物品洗劫一空。正当窃贼意欲开溜之际,被闻讯赶来的警探迎头撞上,当场擒获。据悉,该私宅乃中央某要员的官邸,该要员日前离沪公干,预谋已久的窃贼即乘机而入。截止发稿,警局方面正在对现场进行勘查……
太原路87号,这不是戴笠的官邸吗?穆木修不觉一愣。当今“特务王”的家也有人敢往里闯,此人莫非吃了豹子胆?刚想到这儿,左眼皮子又“噗噗”地跳了起来,气得穆木修甩下报纸,双手捂着眼窝使劲乱搓……
大约子夜时分,常熟路警察分局的值班副分局长王正才被一个匿名电话从睡梦中吵醒。电话里的那人口气蛮横,坚持要和局长通话,接线员不明对方来路,未敢造次,只好乖乖地把电话摇进了局长室。
王正才困思懵懂地拿起话筒,心里甚感恼火,可是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他的脸色就变了,双眼瞪得溜圆:“喂,你是谁?你怎么知……”他还没来得及吐出那个“道”字,对方“咔”地一下把电话挂了。
不管那家伙在电话里说的是真是假,他都不能不认真地履行一回职责。太原路87号,岂是等闲之地,万一真有什么闪失,他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只怕难保。
王正才当即调集警员,火速向太原路赶去。警车在百米之外戛然止 住。王正才正想指挥手下包抄而进,蓦然又多了个心眼:万一电话所报失实,我王正才半夜率部包围戴笠官邸,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只怕到时候长一千张嘴也说不清。王正才左右为难,踌躇不前,愁得在原地打起了转转。正犹疑间,忽见87号门里闪出一个黑影,举止慌张,神态鬼祟。王正才眼尖,一眼瞄定那人路子不正,即命手下过去查问。那人看见冷不丁冒出一群警察,立刻慌了手脚,夺路狂奔。王正才二话不说,率先穷追不舍,众警察于是也呼呼隆隆地紧随其后。
不一会儿,那人已被逼进了一条死弄堂,眼看无路可逃,只好跪地求饶,束手被擒。
87号果然有事。王正才不敢有丝毫怠慢,马上掉头,心急火燎地往回赶。
87号院门洞开,空无一人。走进大厅,王正才傻眼了,堂堂“特务王”的官邸竟然一片狼藉……
戴笠雷霆震怒。一连串的责骂吼得电话听筒簌簌发颤,巢弘不得不把听筒拿远一点,才能勉强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戴笠之所以震怒,不是为了上海的官邸遭窃,而是因为——居然有窃贼被擒?尽管远在京畿(南京)的他一时还弄不清楚被擒的是何等样角色。
巢弘虽然也不清楚那个被常熟路警察分局生擒的家伙的来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自己手下的人。从昨晚到现在,整整三十几个小时过去了,自己没丢一兵一卒。凭这一点,他有恃无恐,相信好戏不会穿绷,不过是多了一点麻烦而已。
听完巢弘的解释,电话那头的戴笠总算雷霆渐息,语调慢慢平缓下 来。一般说来,他对巢弘这员大将还是极为宠信的,不然不会让他坐上军统局特检处处长兼上海别动组组长的交椅,更不会把如此绝密的事情交他去办。“好吧,没出岔子最好。你马上去找宣铁吾,把失窃清单交给他。还有,情况弄清楚后随时向我报告。”
“是!”巢弘毕恭毕敬地放下电话,捋了一把额头上沁出的汗珠,顺手摘下墨镜。他的左眼角处,一道紫色的刀疤,泛着黯然的油光。
完了,完了,老子这回栽狠了!”蜷缩在拘留所冰凉的水泥地上,麻皮老五心里连连叫苦不迭。怪怪的,怎么刚刚出门就会撞上警察呢?就好像知道他麻皮老五该出来了似的,专门张着网候他。莫非帮会里有谁串通了警察故意害他,不然哪会这么巧?可是转念一想也不对,这回他出来没有对谁说呀,为的就是吃独食。
那天下午碰到怪眼张,怪眼张还问他有没有合适的堂口“接财神”。他怕“漏水”,没敢露半句口风。怪眼张和他一向交情不错他都没说,旁人就更别指望了。这一路“线”,他已经来回“踏”了好几天,那幢大洋楼里的人家肉头甚厚,可是“防风”也紧,篱笆墙外老有戴着鸭舌帽的便衣瞎转悠,一看就知道尽是些“大兔羔子”当兵的,再怎么乔妆改扮也没用。可是,说也怪,那天下午不知为甚“大兔羔子”们忽然全没影了,撤了个干干净净,大洋楼里空空落落地断了人气。他去那门前溜达了好几个来回,连个耗子也没见着,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唉,没料想这一干干进了班房……
那晚,天黑以后,一直在周围逛荡的麻皮老五翻墙进了87号,根本就没动篱笆墙上的铜锁,更没砸玻璃。他蹑手蹑脚地掩在树丛里窥测了好一阵,想搞清楚那楼里究竟还有没有人。时光一分一分地捱过,大洋楼里始终漆黑一团,听不到半点人声。正当麻皮老五暗自庆幸,准备动手时,忽听得院门锁“咔嗒”一声开了,走进几个男人,吓得麻皮老五赶紧又缩了回去,趴在树丛里一动也不敢动。
来人的身份不好估量。说他们是客,却能从外到里打开一路门锁,动作娴熟得如同探囊取物;说他们是主,可接下来干的事却让麻皮老五瞠目结舌——先是“咣啷”一声玻璃响,来人把客厅窗户砸了个大窟窿,接着听到一个沙哑的男声说:“去,把门锁撬了。”有人答应着走到院门处,“咕吱咕吱”地撬了起来。
他们和自己难道是一路?麻皮老五暗自思忖。可又不像,哪有先进了院门再撬锁的?脱裤子放屁,犯得着吗?后来那帮人进了房间,大模大样地开灯说话,全无一点避讳。接着房间里便传出一阵稀里哗啦的砸东西声。麻皮老五敛声屏息地到窗前偷瞧——天哪,他们这不是明抢吗?
房间里一片狼藉。有两个家伙正拿着钢锯在锯一只墨绿色的保险箱。其余的几个,有的在扯电话线,有的把铁皮柜里的文件朝外扔,还有一个戴着墨镜、套着皮手套的高个子端着茶几上的杯子,不知在摆弄什么。
一共有五个人。
戴墨镜的大个子摆弄完茶几上的东西,就势在旁边的转角沙发上坐了下来,二郎腿一跷,透着悠闲。突然,他好像被呛了,“吭吭”地咳个不停。他摘下墨镜,掏出手绢擦眼睛。皮老五看见,那人的左眼角 上,有一道紫红色的刀疤……
这帮家伙在大洋楼里前后闯腾了足有两个小时,这才大摇大摆地熄灯走人,然而,也就在这时,麻皮老五发现了一桩让他至今仍然百思不解的怪事——这帮家伙全部空手而归。
这算干啥,费劲拔力地折腾了小半宿,到末了横草不沾,竖草不拿, 两手空空,走了?这不是圣人喝盐卤—明白人干糊涂事吗?麻皮老五实在闹不明白这里面的蹊跷。
又熬了一小会儿,麻皮老五确信周围已经没人,才慢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先在原地伸胳膊踢腿活络一下筋骨,然后像只耗子似的钻进了大洋楼……
麻皮老五不是圣人,不干那号瞪着两眼珠子喝盐卤的怪事、傻事、糊涂事。
萧瑟的寒风刮过街弄,带来了满天的阴霾。又是一场寒流过境,上海降下了一场薄薄的腊月雪。
王正才听市局机要室的哥儿们悄悄告知,戴笠前几天回上海,在百老汇大厦做东,宴请了一身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和市警察局局长二职的宣铁吾。据说觥筹交错间戴老板碍于宣司令的面子不好多说什么,可还是对警察局的工作效率表示了不满,对付一起失窃案竟然到现在也没能理出个头绪。这使宣铁吾感到非常难堪,同时也十分恼火。
戴笠是怎么说的王正才不清楚,但宣铁吾的恼怒他则很快便真真切切地领教了。事情缘于麻皮老五的死于非命。
经过对戴公馆的现场勘察,王正才认定,此案决非一人所为。这一 点,从麻皮老五的口供中也得到了证实—曾经有五个人,先于麻皮老五洗劫了戴公馆。为此,王正才又对现场进行了二度勘察,并从茶几上的一套咖啡壶具中提取到了两枚极有价值的指纹,经与麻皮老五的指纹比照,果然不能吻合。同时,王正才还对烟灰缸里的烟蒂进行了化验,烟蒂上残余的唾液证实了麻皮老五的血型与案犯亦不相同。
王正才兴冲冲地把材料整理成文,连夜向上秉报,然而,就在材料报上去的第二天,麻皮老五突然被人从拘留所里提走,并且很快有消息传来:麻皮老五途中试图逃跑,被押解的警员一枪毙命。王正才怒火中烧,迅即赶到拘留所兴师问罪。他必须知道,谁胆敢未经他的批 准,擅自将重犯押走。拘留所所长在挨了一通狗血喷头的怒骂之后, 怯生生地说:“麻皮老五是宣局长让人带走的。”
宣局长?这怎么可能!王正才将信将疑。他狠狠地瞪一眼拘留所所长道:“你要是撒谎,回头老子非让你蹲班房!”说罢挟着一股余火,直奔四马路(今福州路)市警察局而去。
宣铁吾局长果然揽下了全部责任,并且冲他发开了无名火。说他只知道捡芝麻,不懂得抱西瓜,鼠目寸光!光晓得盯牢个小小地痞麻皮老五顶屁用,既然手头有指纹和血型,为什么不去抓真凶……”
王正才被训懵了,搞不清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宣铁吾从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王正才说:“拿去,这是戴公馆的失窃清单。记住,就从查找失窃物品着手,我会派人来帮你。”
回到分局,王正才打开清单仔细过目,心里不由得暗暗吃惊,那上面开列的全都是国宝级的稀世古董,价值连城,他们在麻皮老五的赃物中压根儿没见着。
第二天,一个戴着墨镜的高个男人找到王正才,拿出宣铁吾的介绍信,说:“我叫巢弘。”
巢弘给他带来了新的破案线索。
穆木修的安南女佣失踪了。消息像阵风似的刮遍了市党部,传得连市党部主任房植也知道了。
“木修兄,听说你金屋藏娇,弄了个外国女人当佣人?”房植和穆木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干部训练班时的同学,交谊笃厚,抗战结束后穆木修脱离军统重返中统,就是由房植一手安排的,所以,他和穆木修说话向来无遮无拦、单刀直入。
穆木修有点窘,关系再好的朋友,对这种话题多少也有点犯忌,“别出我洋相了,什么金屋藏娇,不过是法租界公董局以前的一个安南厨娘。”
“哈哈,你还想赖?”看着穆木修尴尬的样子,房植高兴得哈哈直笑。笑罢,房植的面部表情陡然一转,变得沉郁而严肃。
“听说这个女人跑了?”
“是……不是……”穆木修语无伦次,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木修兄,不是我要干涉你的私生活,干我们这一行的,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一点反常现象,都必须多问一个为什么。”房植是中统的老牌特 工,举止斯文,乍一看像个中学教员,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面善心狠,长于谋略,在中统内部,素有“房诸葛”之美誉。
“那是,那是。”穆木修连连点头,但心里并不以为然。
“不是我夸大其辞,”房植继续道,“你这次‘跳槽’回中统,我担心……”房植欲言又止,下面的话,房植吐不出口。无论是他还是穆木修,其实心里都很清楚,无论中统或者军统,一向都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跳槽”无异于背叛,而对背叛者,多年来水火不相容的两家从来就是杀不容赦的。
“房兄放心,一切我自会小心斟酌,谨慎从事。”见房植为自己担心, 穆木修心存感念。
由于一个女佣的失踪而引出这样一个严峻的话题,是穆木修始料未及的。在他看来,黎的出走其实很好解释,原因恐怕就在于自己对她的骚扰过于性急所致。自己本可以再温柔一点,再甜蜜一点,让黎先获得一种安全感,然后在柔情蜜意中迫其就范,诱其入彀……黎出走的原因就这么简单。穆木修心里洞若观火、透似明镜。
可是这样的原因能对房植摊牌吗?说不出口嘛。
至于军统方面——抗战期间穆木修曾经在他们的上海别动组干过,能不懂他们的规矩吗?“凡军统成员不得与中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通婚, 违者判7年徒刑。”军统内部确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如今不管用了。经历了抗战,双方共同辅佐委员长,早捐弃前嫌了嘛。再说,自己也并非与CC成员通婚,只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改换门庭罢了。军统失去一个不受重用的成员,何怒之有?事实上,戴笠先生还是颇有点人情味,很重旧部情谊的嘛。
穆木修之所以有此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民国35年阳历年,也就是元旦的下午,戴笠以“抗战同志团拜会”的名义,在太原路87号召集部下及有关方面聚首,共贺新禧。承蒙不弃, 已经“跳槽”另栖的穆木修也接到了请帖。在接到请帖的最初一瞬,穆木修不免诚惶诚恐,感动得差点掉泪。然而转念一想,当初自己在军统麾下受命听差时,几曾得到过戴老板的如此礼遇?如今择木另栖, 反倒受人厚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自己“跳槽”跳对了!不然永远只能是戴老板手下的末流角色,永远别想出人头地。
怀着重新发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喜悦,穆木修底气十足地跨进戴公馆。晚宴既毕,戴笠送走其他人士,独独留下了抗战时期上海别动组的几员大将,有巢弘,也有他。把他们请进楼上小客厅,说要和弟兄们叙叙旧。戴笠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动了真情,说起话来声音都有些发颤:“在坐的诸位都、都是我的老部下,抗战时期曾……经坚持敌后, 浴血杀敌,劳、劳苦功高。今年元旦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一岁之始谓之元,你……们也是我军统的元,元勋,元……来来来,我 要和你们这些元老再干一杯……你们都是我军统的宝贝。”
说到“宝贝”,戴笠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巢弘道:“去,把楼下保险箱里的宝贝拿……拿来,让弟兄们见识见识。”
巢弘应声下楼,不一会儿抱上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箱子。
戴笠兴致勃勃地接过箱子,依次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拿出来让大家过目:
“这块玉佩叫‘战国玉龙’,它用青玉琢成。间杂赭黄色的青玉可是旷世 奇材呀。再看这件,它叫‘汉代玉翁仲’,也是稀世珍品,极其罕见, 后人极少见到真品,还以为翁仲是老人,实际上真正的汉代玉翁仲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件就是小伙子……”
接着,戴笠又摆出了唐三彩骆驼、宋官窑瓶、春秋铜盘、宣德炉等十几件古董,狭长的茶几上顿时变得珠光宝气、光彩耀目。
戴笠指着茶几道:“这些宝贝前些年全部不幸落入倭寇之手,胜利之后才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被我敌伪产业清理局悉数收缴。为防不测, 他们暂时交我代为保管。看到这些宝贝,我就想起了在座的诸位。没有你们的浴血杀敌,就没有它们的重返故园。为此,我要代表蒋委员长,代表党国,也代表这些宝贝,敬诸位一杯。”
放下酒杯,戴笠指着茶几上的“汉代玉翁仲”说:“这件宝贝像你们在座的一个人。”
“谁?”众人诧异。
戴笠一指穆木修:“像小穆嘛,哈哈哈……” 众人附和:“像、像,哈哈哈……”
穆木修最终也没能弄明白,戴笠这一指乃大有深意焉。
史载:翁仲,秦皇卫士,膂力过人,武艺超群;死后,秦皇为求其庇护,铜铸其像置于宫门外。汉代帝王,多以玉琢其形,殉葬于墓棺。
民国35年2月21日傍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调查室主任穆木修在其寓所内,被市警察局常熟路分局以涉嫌戴公馆失窃案的罪名逮捕。此后数日,穆木修其人成为沪上传媒的报道热点。
《申报》(2月22日讯):昨日傍晚,常熟路分局警探在穆姓人家原帮佣女工黎王氏的引领下,在穆的寓所内将其逮捕,并当场从寓所百叶窗的木框里,抄出“汉代玉翁仲”一件。经王正才副局长辨认,确信此件即太原路87号失窃古董之一。黎王氏哭诉,穆曾以此古董诱骗于她,欲施非礼,许愿一俟古董脱手,即双双逃往东南亚成婚。黎王氏乃温州人氏,一口当地土话令记者束手无策,经翻译始与交流……
《申报》(2月23日讯):警局发言人再次证实,从穆某人家中搜出的“汉代玉翁仲”,确系上月太原路中央某要员家中失窃之物。同时失窃的还有先秦以来的历代珍贵文物十余件,件件价值连城。警局发言人称,该批珍宝系敌伪产业清理局的寄存物品,当年曾悉数沦落倭寇之手,光复后始归故园,不料遭党内的败类垂涎打劫,再度蒙尘,殊属不幸。据悉,其余珍宝尚下落不明……
《正言报》(2月23日讯)本报记者日前就太原路失窃案专访了常熟路警察分局王正才副局长。王正才应记者要求,披露了本案侦破时的若干秘闻。在警局对穆犯正式施行逮捕前,已经秘密地掌握了穆犯的指纹与血型,经与现场遗痕比照,吻合无二。在现代高超的科学技术面前,大盗嘴脸暴露无遗……
《铁报》(3月1日讯):现代公正的法律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窃宝大盗、前市党部官员穆木修案,已由市警察局移交地检处, 据信不久将由地检处向特刑庭提起公诉……
然而,就在穆木修案即将盖棺论定之时,1946年3月17日上午,“特务王”戴笠的座机在南京郊外江宁县戴山触山坠落,机毁人亡。
穆案于是出现转机,终于不了了之。
据民间传说,戴机坠毁时,同机载国宝10箱,一并遭大火焚毁,独遗“汉代玉翁仲”一件,纤毫未损,后伴戴笠尸骸,殉葬于黄土之下……
有目击者言:穆案中的“汉代玉翁仲”,长髯垂胸,老态龙钟。据此推断,真正的“汉代玉翁仲”即面部造像年轻者,当为戴笠墓冢中的那一件……
戴笠移花接木,早已用赝品将真品换去了。也许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
(责编/章慧敏)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