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居民消费率为何这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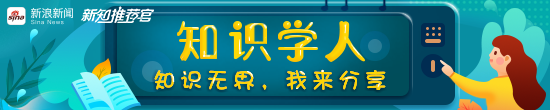

· 殷剑峰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数 6k+ ·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那么,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最终,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也将难以为继。
观察2012~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
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两大因素
对GDP需求结构的跨国比较似乎表明,中国人像巴尔扎克笔下吝啬的葛朗台,贪恋财富,却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真的是中国人过于“吝啬”吗?我们可以将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分解:
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
=(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
= 居民消费倾向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所以,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消费倾向,即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
其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在主要国家中,中美两国的总需求结构正好相反,中国是投资高、消费低,美国是消费高、投资低。在2001~2020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
那么,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消费倾向过低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呢?是前者。因为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收入高,收入稳定,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而且,观察新冠疫情前的数据可以发现,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居民消费倾向就在不断上升,相应的,居民储蓄倾向(储蓄/可支配收入)不断下降。
这也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在人达峰前的人口红利阶段,获得收入、进而储蓄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多,因而居民部门总体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在人达峰之后,退休的老年人口开始消费此前的储蓄,这必然导致消费倾向上升、储蓄倾向下降。
然而,从人达峰之后的2012年算起,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还低于2012年。
所以,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吝啬”,实在是囊中羞涩,“没钱”啊。可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位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么,“钱”去哪儿了呢?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问题。

三种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
一些人以为,与做大蛋糕相比,分蛋糕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分蛋糕也挺复杂。
这里有三种分法:
第一,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
第三,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
三种分法中,最难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
就第一种分配而言,在《资本论》中,通篇描述的都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收入过低的工人阶级缺乏消费的能力,从而反过来又导致资本的过剩。
一些人据此也以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原因就在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因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成了自然的政策选项。然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确实,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的取代,在许多国家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但是,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
以2010~2019年部分国家数据为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这一数值虽然比英、美、法、德四国要低,但高于其余11个国家。在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中国劳动报酬占比都是最高。
所以,劳动报酬占比不是居民“没钱”的原因,而且,这也解释不了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例如,巴西劳动报酬占比比中国略低,墨西哥劳动报酬占比则低至37%,但两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高达64%左右。
与第一种收入分配直接相关的是第二种收入分配,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资本剥削劳动的结果就是,在居民部门内部,形成了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少数富人和饥寒交迫的大多数穷人。
富人,哪怕骄奢淫逸,也消费不完占有的财富;穷人,哪怕消费倾向再高,也无钱消费。于是,在每个人的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导致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然而,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基尼系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该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比较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五。这表明,在这种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确实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无论是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国家,如英国、印度、日本等,还是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居民消费率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
而且,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美国,其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中国。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既解释不了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也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无关。
第三种收入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等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比较2012~202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
所以,中国居民“没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两个途径
那么,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呢?
进一步观察中美居民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问题的答案。中美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有所差异,但大体可以归于三项:
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 + 财产收入 + 经常转移
其中,劳动报酬主要是工资收入,在中国,这一项还包括与工资收入相差不多的增加值(可以理解为小微企业、个体户的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经常转移是政府通过再分配给予居民的收入,这等于居民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社会福利补助、再扣除缴纳的收入税和社保缴款之后的净额。
比较中美居民的三项收入,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只占4%强,经常转移收入几乎可以忽略。相反,在美国居民的收入中,财产收入占到22%,经常转移也达到9%。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两个途径就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和经常转移收入——这两个途径都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有关。
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首先是要让居民部门拥有财产。如果不拥有财产,怎么能够获得财产收入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资本所有结构中,私人资本大幅上升,但直至2019年私人资本占比也只有64%,国有资本(即广义政府拥有的资本)占比高达36%。相比之下,在美国的资本所有结构中,2019年私人资本占到83%的份额。
在资产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财产收入的方法之二是改善居民的财产结构。观察中美居民的财产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低的第二个症结,即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在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这两项均是低收益的资产。
相反,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占比很高,金融资产中权益类资产和持有的机构投资者资产(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寿险等)占比很高。算起来,在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直接和通过机构投资者间接持有的权益类资产达到50%以上——这是居民财产收入较高的另外一个原因。
除了财产收入之外,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加直接和迫切的途径是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财政的职能之一就是再分配,即利用收缴的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反补给居民部门中的弱势群体。
然而,观察中国经常转移的部门分布,政府部门得到的经常转移收入常年以来都远远高于居民部门。在2018年和2019年,居民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甚至是负值。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虽然政府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8万亿,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上升,但也只有区区不过2000亿。
这种景象与新冠疫情期间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0年和2021年两年中,美国政府财政支出较疫情前增加了共计16万亿美元,其中支付给居民的个人福利增加了共计11万亿美元,占全部新增财政支出的69%。所以,在疫情封控后,美国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因为“有钱”啊。当然,庞大的财政福利支出也造成了高涨的CPI——但与消费萎缩、经济低迷相比,这种代价还是值得的。
关于中国财政存在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初次分配环节中,财政通过较高的宏观税负占有了较大比重的收入,在再分配环节,又通过经常转移将部分收入转移给了自己。
所以,财政职能的异化是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根本症结。当前的财政体制已经到了需要做根本调整和改革的境地了。
财政体制的三个问题——以养人为主的“吃饭财政”、过多介入经济事务的“投资财政”、债务快速累积的“窟窿财政”,都需要认真加以正视并解决。
总之,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乃至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因为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体制性掣肘。在三年疫情之后,随着就业的提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居民消费当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不能对之期待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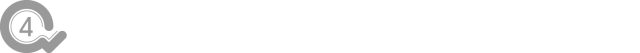
财政的“钱”去哪了?
以上论述了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过高是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过低乃至居民消费率过低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这里的统计还低估了政府部门收入。如果考虑到在统计上被计入到企业部门收入、但实际上属于政府部门收入的国有土地出让金,那么,在2012~2020年间,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上升到25%。
既然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那么,财政的“钱”都去哪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财政支出的数据进行分析。
财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大项。按照我国国民账户的统计规则,政府消费被界定为“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从字面理解,并不能知道究竟何为政府消费,相关统计也从未公布过政府消费的具体内容。
根据世界银行关于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政府消费主要是用于如下几项的财政支出:雇员报酬、商品和服务支出、补贴和其他转移。
但是,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统计中,唯独没有中国财政支出的数据(财政收入和政府负债的数据都有)。
参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并对照支出法GDP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对政府消费进行了推算。为了可阅读性,这里省却了具体的技术细节,直接给出统计的结果:
政府消费=
劳动报酬支出 + 社保福利救助支出 + 统计误差
上式中,统计误差为支出法GDP中政府消费统计与本文统计的差额,在2018~2020年三年中统计误差平均不到5%。
在财政支出中,政府投资相对透明。政府投资包括两块:其一,政府的资本形成,即政府直接从事的投资;其二,政府的资本转移,即政府将资金转移给企业,通过企业间接进行的投资。
于是,整个政府的支出就是:
政府支出 = 政府消费 + 政府投资
=(劳动报酬+社保福利救助+统计误差)+(资本形成+资本转移)
将本文统计的政府支出与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支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几乎完全相等。例如,2020年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支出为24.57万亿,本文统计的政府支出为24.41万亿。所以,统计方法上应该没有问题。
观察整个财政支出的结构,在2012~2020年间,基本上呈现出“三分天下”的格局:劳动报酬占比34%,社保福利救助占比32%,投资(资本形成与资本转移之和)占比32%。
至于统计误差,只占2%。那么,这种三分天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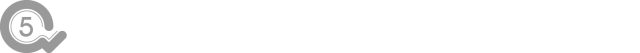
财政支出的跨国比较
中国当下的财政体制延续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基本框架。在笔者的《金融大变革》一书中,将这种财政体制称为“增长型财政体制”,以对应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
除了央地分权结构存在差异外,两种财政体制的关键区别在于财政支出。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扮演的是“无形之手”的角色,主要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因而财政支出以社会福利支出为主。
在增长型财政体制下,政府扮演的是“援助之手”的角色,财政支出以政府投资为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有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作为。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的成熟,财政体制最终应该转向公共财政。然而,对15个发达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比较表明,这种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甚至“援助之手”的职能也出现了异化。
从财政支出的跨国比较看,近些年中国财政体制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抠门财政”。
跨国比较的第一个发现是,中国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比非常低。在2012~2020年间,中国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32%,在15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中国的福利支出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财政体制的差异,这尚可以理解,但是,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尤其是发展水平比中国差很多的印度,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第二,“投资财政”。
跨国比较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的比重非常高。以新冠疫情前八年的平均数据看,全部投资中,中国的政府投资占比高达36.5%,居于第二位的希腊也高达31%,日本和印度超过了20%,剩下11个国家都在20%以下。所以,中国政府投资的比重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阶段相近、甚至发展水平不如我们的国家。而高投资率的背后是政府投资过多。
第三,“吃饭财政”。
跨国比较的第三个发现是,中国财政支出中人员费用的占比奇高。从2012~2020年的平均数据看,中国财政支出中雇员报酬占比高达34%,与居于第二位的希腊相比,高出了13个百分点,是其余13个国家的2倍到5倍。
这表明,中国政府支出的特征并不仅仅是发展阶段差异所致,其背后是财政职能的异化。尤其是财政支出中政府投资占比较高、人员费用占比奇高的特征,说明政府这只“援助之手”已经干了太多本应该交给市场干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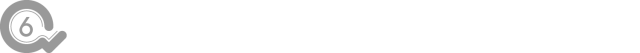
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率
中国财政支出的这三个特点不仅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异化,也与近些年政府债务压力的不断加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首先是政府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收不抵支,就得靠新增负债,即:
财政支出 = 政府可支配收入 + 新增负债
观察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中可支配收入和新增负债的比重,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对债务依赖程度的显著上升是在2015年之后:2015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支撑的政府支出下降到不足90%,到了2020年财政支出中只有61%靠的是当年收入,剩下近30%的支出依靠债务融资。
财政收不抵支,以至于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这一方面与一如既往的“投资财政”有关,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吃饭财政”。2015年之后,劳动报酬支出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20年已经超过了60%。近些年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没有大的提升(甚至可能是下降的),因此,财政劳动报酬支出的比重上升只能说明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这也解释了为何近些年报考公务员如此热门。
除了债务压力之外,每年财政收不抵支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实际发生的赤字率早已经超过了3%的赤字率红线。
观察利用资金流量表统计的赤字率(赤字率:资金流量表)和财政部统计的赤字率(赤字率:财政部统计),可以看到,1992年以来两种赤字率的走势完全相同,只是程度有差异,尤其是在经济遭遇冲击时,前者更大。
例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直至2003年期间,利用资金流量表统计的赤字率都超过了3%。自2015年之后,这一赤字率再次超过了3%,并且不断扩大。实际上,在2020年和2021年,即使是财政部统计的赤字率也过了3%的红线。所以,坚守3%的赤字率已经无意义,也无可能。
总之,1994年分税制建立起来的财政体制框架,在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做彻底改革的境地了。不仅财政的职能出现异化,而且,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的央地财政关系也是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溯源。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