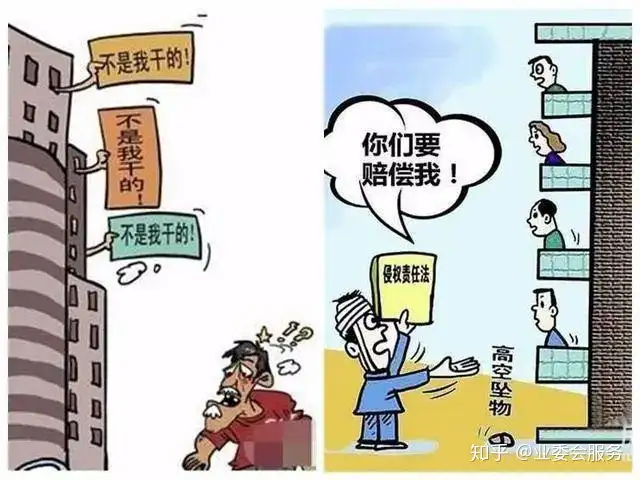李霖灿:中国画断代研究例
绪言
在博物院中工作久了,时常有朋友带了画来叫我们辨别它的真伪,鉴定它的年代。遇到这种场合,我常有两种不同的心情:首先是非常之高兴,奇文共欣赏,自是人间之至乐。然而接踵而至的每每就是惭愧,因为我总觉得解释的没条没理,不能使朋友们称心满意。
这样的情况遇见多了,自己也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彻底之计,反躬自省,若不自己先有一套清晰的条例可资研讨,那怎能怪朋友的追根问底?我们不是也曾以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苦恼过不少的专家来么?如今我们知道的这一点点常识,也可以说正是从他们讨教和摸索印证而辛苦得来,怎可以再叫我们的朋友也来吃同样的苦头?
因此,我思索了很久,就若干年来的浅浅所得,排比董理了一下,为中国画的断代问题试拟了六项标准。只要有朋友拿画来叫我鉴定,我便以此断代六法作为纲要,与之商讨周旋。效果竟然不错,虽不能说毫无夹缠,但比以往的天南地北汗漫无归的局面是好得多了。
由此我得到了一项很重要的启示,大概是以往的方法上有问题,所以才使我国绘画的鉴定老是混淆不清。如今玄学式研究方法的时代已该过去,让我们用这项严谨的新方法来试验一番,看能不能给中国画的断代问题,甚至于中国文化史的若干问题,来投射出一些新的曙光。
这一项疑问潜伏在我心中已很久了,就是讲我国文化史的人常常是有意地省略去绘画这一环。艺术是文化的高层建筑,绘画是艺术上重要的一目,我国绘画的积存虽迭经变故,但在质和量上仍极丰富,讲历史的学者为什么要如此地视而不见或故意地避而不用呢?——试想在讲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把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职贡图》揭示出来(《故宫名画三百种》上第一图有彩色版,可供鉴赏)说明这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南方的林邑、婆利、罗刹三国联合到长安朝贡时的传真写照(那时尚没有摄影机,所以画家就来代替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意味该多真切!若再加上鹦鹉怕寒、太宗放生的有趣穿插,那唐书上的记载简直似电影一样的活动起来了,多好!(请参看拙文《阎立本〈职贡图)》,《大陆杂志》12卷2期。)
同样的话,假如讲汉代的史实,悬挂出《朱云折槛图》和《袁盎却坐图》(《故宫名画三百种)》134、135图)来对图细讲,多么实感逼人!讲到郭子仪的丰功伟业时,展开《免胄图》(《三百种》85图)来依画细谈该多动人!《明皇幸蜀图》的各式图本,简直把这位皇帝的戏剧生涯表现得如亲炙面对。其他如讲陶渊明的田园生涯,把纽约都会艺术馆的《归去来卷》借来指点,多少生动!苏东坡的《后赤壁赋》,故宫有几幅手卷描绘得栩栩如生!说到北宋的文化造诣,选出几幅范宽、郭熙的巨轴山水悬挂起来,当亦能令听众醒目、讲堂生色!—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如此配合使用呢?
说破了很简单,原来这正与中国画的断代问题有关系。虽然诚如《故宫书画录》上所示的,现存北沟的名画,共有为3887件之多(若将692件册页,平均每件加增八开计算,共当为9423点,若合计长卷中之独立单位当近万点),但它的断代题名大都是根据原标签而来,尚未经过严格的对证考验。为了善价而沽或托古自高,这些标签常常有名不副实的现象发生。受过科学训练的历史学家洞悉个中原委,深恐采用了伪书赝鼎致使他们的工作受拖累,因此便取了一种宁缺毋滥的审慎态度,几乎是因噎废食地将这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一刀割置之于“不予考虑”的冷宫之中!
亦不要去抱怨历史学家的残酷,有切肤之痛及疚心之愧的却正是我们这些在博物馆中的工作人员。多少年来,日夕摩挲这批宝藏,别人尚可借词推脱,我们不是理所当然,早该把这批“国之瑰宝”董理出一些头绪来么?
一张明朝的画,标签题作宋人,自然是张假画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厘订出若干鉴定的标准,追究出它的本来面目,证明它是明代某派或某人的作品,那这幅画岂不是又可以成为第一等的真实史料了吗?所以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中国画的断代研究。若是经过大家的审慎商讨,制定出若干共同可用的尺度,对现存吉峰山下的两院名画(约当全世界这项收藏的四分之三),一件一件地加以审查丈量,到最后把它们排比得各得其所,然后再参用一些国外的重要资料,那信而可征的一部中国绘画史不是就可以写定了么?到那时候,矜持的历史学家自然会乐于采用,中国的文化史亦必然因之而更臻完美了。
故宫、台北故宫两博物院所藏的这批名画,一向都为人视作“欣赏的对象”,却还没有人指点出这是“宝贵的史料”。其实这多么简单明了,这批名画全出古人之手,数量有四千件或一万点之多,时代包涵唐、宋、元、明、清有千余年之久,怎能说不是一批珍贵的史料?如今只因为这一点点断代不明的缺陷,遂遭弃置而不用,多么令人惋惜!
为此,我愿意以“书呆”“画迷”的双重身份,在这里郑重宣布:甲骨、汉简、敦煌和大库档案号称为近代史料的四大发现,现在呢?北沟名画,应与之并列而为第五,因为中国绘画的信史定要由此产生。
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时代中,这一大批史料竟没有人发现到它的重要,毋宁说是一件“奇迹”。当然,艺术家不愿做到,史学家不易做到,是令这批珠玉生尘湮没至今的最大原因。艺术家虽懂绘画,但却不耐精细的研讨排比;史学家有这一套好方法,却对艺术的了解不免隔了一层。记得向觉明先生有一次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敦煌艺术”,多好的一个题!我冒雨赶往听讲。听后的感觉是:这是一篇很好的敦煌“史”的讲演,但对艺术方面,除了“铁线描很有力”之外,缺少了深邃的发挥,实在令我这个艺专的学生听得不过瘾。因此,我想到了书呆而兼画迷的双重身份也是不易得到的。所以我便以此特殊身份,在这里郑重宣布这第五史料的重大发现,不知大家也同意这项新颖说法还有些道理否?!
成败的关键,全在我们能不能给这批资料以正确的断代,以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式方法自为我们所不取,骨董商人那种混沌感觉方法亦待改进(他们的经验是有的,我们亦很重视,但要用清晰的条理好好地爬梳一下)。现在的原则是恰反其道而行,弃彼玄奥,还我平实,揭示出一些清浅明白、人人可用的新尺度,而且以这项新的标准对两院及存世的中国古画,重做一番正确评价的大工作,好来建立起中国绘画史的新事业。
或许有人要笑我们的不自量力,但我们却自信甚坚,用新方法治那些新史料的伟大成就昭昭在目,这就是我们必能有所报命的最好保证—一我们立论之始,先求平实稳固,虽像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明晰可循,人人可以增添,时时都可覆按,一有结果,便是后来踏脚的新基石。如此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将来的成就一定可以堆积得博厚高深。以往我国绘画史的浑沌局面必可因此而澄清,到最后一定众擎易举地完成我国文艺复兴之大业。
若将此事向更深远处推展,中国绘画是世界艺术中重要的一环,因此,中国绘画史的写定一定会启迪到中国绘画理论的阐明,而这道江河宏阔的艺术理论体系的阐明,也理所当然地会对混乱的世界艺坛发生重大的澄清作用的。那么,这项新标准的建立和使用,其效果真可以说是音响宏阔了。
当然,作者一人所见必定不能周全,所以声明在先,在这六项标准之外,欢迎大家见仁见智地增添;在这六项之内,亦请赐珠赐玉地损益删订。我的这篇文字只是代大家试拟了一项草案,我满怀希望地在这里抛砖引玉,权作登高划界之一呼!
鉴定一两张古画,也可以说是其事甚小,但全部古画的总断代,中国绘画史的重写定,中国绘画理论体系的再建立,却都是我国文艺复兴的大事业。为了玉成此一大事,我呼吁各方面的专家硕学都来贡献他们的宝贵经验和伟大的力量。
断代六法举例
前些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字,题目叫作《中国绘画的六法新论》(载《学术季刊》6卷4期),那是对谢赫的绘事六法有所订正,目的是在讲中国画的欣赏,侧重在“美”;现在这篇文字是讲中国画之鉴定,目的在求“真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前者可以说它是“文艺的”,后者则是“科学的”。
每一幅中国画都可以作此两面观,然后交相融会而止于至“善”。所以这两篇文字可以说是姊妹篇,她们的目的在树植起重整中国绘画的两大柱石,要以此揭橥出中国文艺复兴时代之来临。
展开一幅图画,大家在赞赏之余,进而到探讨它的正确年代的时候,这就涉及本文范围内的重点了。我从多年来追随各位先进学到的经验中,和自己读画印证的思考里,把一幅中国画的断代问题,贯通地归纳为六项新标准,这在上一章已经道及,现在举例诠释于下:
一、质料之观察
艺术家表达他的情怀,不能不有所凭借。画家所用的绢纸笔墨颜料等物,它们的质地形制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演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若能洞悉个中原委,那当然能给我们不少断代的标准。
譬如说画绢,这是我国古代画家最常用的一项凭借,这里面就有不少的课题,值得我们去探讨:放射性碳素14的年代测定法,现在我们国内虽还不能办到,但这项测年方法日趋精密,必能对我国绘画的断代问题有重大的贡献,自是值得我们赶快去研究学习。紫外光线对画绢颜料修补增添的痕迹,有目光不能见的敏锐,亦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新课题。
而且除此之外,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如绢面粗细的程度和时代配合的关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探讨:我国画史上的纪录中有“唐人五代绢素粗厚,宋绢轻细”及“五代绢或粗如布”的说法,但是粗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平方厘米中几经几纬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见人仔细研究过。若用近代的工具和方法,将可靠的唐宋元明的绢放大照相来研究,我相信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收获。什么唐代的生绢,五代双缕方眼之蜀绢,宋代之院绢、独梭绢,元代有名之宓机绢都可以由此而得到正确的辨认。一旦得有成果,便成为人人可用的尺度,这对于唐、五代、宋古画的鉴别尤有价值,因为今人虽可以用古绢,但古人用晚期的绢布乃是不可能的事幅画在宓机绢上的图画,却标上王维、韩幹的大名,那真伪立刻就可以判定。
同样,绢布幅面的宽狭,绢丝的扭转情况,经纬的组合方式……一一都是可注意研究的现象。有这么多的资料堆积在这里,去探求一项常数和时代配合的关系,那应该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一旦得到结论,那就是断代的基石,可以拿它来对存世画件作精密的丈量。也可以在此基石上继续深造,再研究出更精密可用的新标准来。新旧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此:旧式方法是不易言传、人亡政息的,新的方法则浅近易解、人人可用而又可以精益求精的。
再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挂轴是由移动壁画及宗教上的帧画演变而来的,所以幅面略阔的挂轴,在古代多是拼接数幅狭绢而成的。古人诗中这项例证很多,如韩愈的《桃源图》诗:“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裴楷的《桃花图》诗:“能向鲛绡四幅中,丹青暗与春争工。”大愚和尚乞荆浩画诗:“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惟要两株松。”刘鳌咏李成山水:“六幅冰绡挂翠庭,危峰叠嶂斗峥嵘。”陆放翁诗:“峰顶夕阳烟际水,分明六幅巨然山。”……都是告诉我们这种巨迹山水,大都是拼接而成了,这是很合理的一项推测,那时人工织绢,腕力所限,不易过宽,所以要画大幅的挂轴屏障那除了拼接之外,实在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看董源、范宽、郭熙等的存世巨迹,亦都支持这项推断,如董源的《龙宿郊民》和李唐的《万壑松风》都是三接,荆浩的《匡庐图》关仝的《山溪待度》、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萧照的《山腰楼观》、李迪的《风雨归牧》、苏汉臣的《秋庭婴戏》……都是二接。这在当时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特别措置,想不到后来竟可以成为一项断代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悬挂起赫赫有的《洞天山堂图》巨轴来印证一番,名这幅名画我们对它可以说是倾仰已久面且也怀疑已久。倾仰的是它的造诣,杯疑的是它的年代。由画面的技法来讲,山头上一派米家点子,很像是宋代以后的作品。标签和题践上都说是五代董源,但是既无签名,又无可靠的宋代收藏印玺,实在没法使我们相信皈依。如今再仔细观察这幅画绢竟是全幅,没有拼接,这与上述的常例来比较,显出了它的不一致来。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在五代时候,例外地有一张宽绢,又恰巧地为董源所得。却愿意先作合乎情理的推测,这幅《洞天山堂图》,恐怕只是后于董源的一幅仿作—于是画绢的初步研究,在这里就显示出它的功用:它使一幅标签五代人的名画,退归到它应得的晚期地位上;至少,它使我们提醒了怀疑,这就是能得到真理的开始。
到什么时候,才有了所谓的宽绢呢?这问题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研究出结论,但是元代陆广(天游)有幅《仙山楼观》的立轴,在《故宫书画录》卷五上有著录,董其昌在诗塘之上,有一段跋语说:“陆天游画一幅,好事者离为二轴。玉水先得一轴,凡十余年,又得其副。合之双美,遂若雌雄之剑,复聚延津,亦奇矣。”
下面边幅又有李日华之题识:
“陆天游画品,在幼文、云西间,以萧散幽淡为宗,若阔幅雄肆之笔,绝不易得也。玉水此帧,乃联素为之者,先得其左,又得其右,吻然延津之合也奇甚奇甚!”
所谓的联素我以为就是说这幅大画乃是由两幅狭绢拼接而成——可能正是由于拼接得不好,历时稍久,合缝松脱,遂使画商动了一画两卖的念头。
幸亏这幅大画到头来分而复合,这才使我们得知原有这么一段公案,所谓的“奇甚奇甚”,大可借来为我们一用,正是由于这项“分久必合”的奇事,才使我们知道,至少在元代,大幅巨迹的画绢都还是有拼接的。
吴镇的许多画迹,亦都支持这项论断,如他有名的《双松图》《渔父图》等都是双拼—可知观察画绢的拼接与否,这原是一件很简单(只要一把尺子即可),但同时又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一旦得有结论,马上就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同样,画绢的颜色,若经过精密的研究后,亦必可能成为断代的一项标准。商人为作假画,时常用特殊的技法把绢做黑、染黑或熏黑,使人一眼看去,灰黯破旧,好像是古画一样。但是这乃“人工速成之法”,稍为留心,不难辨认出这与真正古画历尽沧桑的风尘之色虽相似而实不同。
元代的王思善氏曾说:“古画绢色淡墨,自有一种古香可爱。惟佛像有香烟熏黑者多伪作,取香烟沥或用灶烟捣碎煎汁染绢,其色黄而不精彩。”可知古人早已留意及此。我们若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细心研究,分辨这二者之差异,应不甚难。所以一幅古画,如巨然的《秋山问道》郭熙的《早春》,那上面都有一种灰青感觉的风尘之色,这是历年久远逐渐形成的。若拿韦偃《双骑图》、(《三百种》17图)的绢色来相比,那上面似熏染过的黑色就比较可疑得多了。当然,现今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探讨到一项人人可用的简便尺度(如色谱编号的分析),但是显然无疑,这也是很好的一项断代标准,而且这里边也真的是大有可为。
宋代之后,画家渐多用纸,于是纸就同绢一样,若通过精密的研究,亦能成为断代的标准。譬如说,有名的澄心堂纸始于南唐,那么,假如我们拣出一帧澄心堂纸来做标本,那就可以成为断代的标尺,因为早于南唐的书画名家,都是不能使用这种名纸的。
恰巧在故宫的收藏里,正有这么帧标准的标本,见于《故官书画录》卷三:
“澄心堂纸一幅,阔狭厚薄皆类此乃佳,工者不愿为,又恐不能为之。试与厚值,莫得之。见其楮细,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阳日。襄书。”(《宋四家真迹册》第八,蔡襄尺牍。)那么,这一张纸就是宝贝,若见到王维、卢鸿的画,竟是画在这种澄心堂的纸上,那便不用考虑,立刻可以判定它是赝品。同样,画史上说,李龙眠自作,则用澄心堂纸。若这项纪录可靠,那对李龙眠真迹的考定,澄心堂纸亦可以发挥鉴别的作用的。
同样的“金粟山”藏经纸始于大中祥符间,江南之竹纸亦始于北宋,苏东坡谓“今人以竹制纸,为古时所未有”,便是明证。其他如元时之罗纹纸、江西之白藤纸及清江纸等,若能一一研究出其分辨之特征,都同样可以成为鉴定年代的好资料。因为后来作伪之人,或由于古纸不易觅得,或由于疏忽方便,每每就地取材因时致用,于是在精细鉴别之下就会露出破绽来了。
笔亦同样地可以研究,因为不同的笔会生出不同的笔触(笔踪),考察清楚了其中的关联,亦可用为断代之一助。
如唐时书画家所用的多为“短锋鸡距笔”,所以柳公权才嫌它出锋太短过于劲硬,因而改求其长而柔者,这便是种较长锋的笔。到北宋苏东坡的时代,有诸葛高能做鼠须笔及长心笔,严永能制獭毛无心枣核笔,吴无至则作“无心散卓笔”普行于宋代天下……这许多不同形态的笔,若能研究清楚其演变和表现在画面上的特征,那对古画的鉴别,毫无疑义也是极其有用的。
墨在中国画坛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谓的“水墨为尚”“墨分五彩”都是说明墨色在画面上的任务重大。所以历代书画大家对文房四宝中的墨都很注意,而且有一些书画家还要亲自下手来做墨,苏东坡的墨灶失慎就是有名的例证。
墨的做法,由其所用的原料上来分,有松烟及油烟两大类:唐、五代、北宋多用松烟,所以墨色轻润而有光彩。
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张遇制御墨,始用油烟。这些记录,应当可靠,所以墨色显然也可以成为断代的一项标准。因为松烟、油烟分辨不难(当然,这还是需要仔细地研究,然后才可以考定出一些简便易识的标准),若遇到用油烟画的范宽《秋山图》,我们自然要提高警觉了。
若作更深的探讨,如松烟的地理分布亦可作为专题的研究。易州和上党之松不同,其烟亦可能不同,若我们的方法精密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亦有希望可以区别古墨的原产地和它的特殊光泽,那自然对断代的鉴别是更有用了——其他如有名的李廷珪墨、张遇之龙香剂墨、金章宗之苏合油烟墨¨一一都是可研究的对象。若能一一为之制定出识别之标准,那对我们的绘画断代必能有所帮助。
我们看明代大部分的画,总觉得它们面上有一层灰灰污黑的墨色,若和宋画的墨色照人来相对比,二者之不同显然可见。我推想大部分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出在墨锭的差异上(当然,纸组之不同亦是一项原因),松烟和油烟之不同,在这里当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日后精密的研究,定能为我这项预测带来正确的答案。
笔墨纸绢之外,所谓的文房四宝还有砚石一项。砚的形态、质地,原也可以影响到作品的表现,但那对书法家的关系较大,对画家尚不见重要。所以砚石本身虽也有它的沧桑演变史,但与绘画断代关系疏远,于此从略。
文房四宝之外,还有八宝印泥亦可研作断代之用。这也是一项好题目,若能用科学的方法辨别出古今印泥色泽之不同,或其调溶剂因年代而变化的程度,那便也是很好用的断代标尺。听说这项研究和纸的分析,已有国外学人着手试验,谨在这里祝祷他们早日成功。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见到了由绘画材料上来寻求断代的标准,真是前程宏阔大有可为的。这断代六法中的第一法有它独特的长处,那就是对象具体,判断客观,有大可展拓的新园地,无玄学争论之乱夹缠。一张明朝绢上的图画,不怕它题上宋、元大家的赫赫头衔,事实上的证明,它不可能是李公麟或黄公望,却只能是姚公绶或周公瑕,因为宋、元人没法使用明朝的画绢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项断代标准使用的限制也在这里,就是它只能作消极的否定却不能作积极的证明。一张元朝的画绢,我们只能用来否定这是唐、宋人的作品,却不能积极地证明这必然是元朝人的作品,或证明这绝不是明、清人的手笔。因为前人固然没法用后来的绢纸,但后人用前代的纸绢笔墨那是很可能的事。何况我国书画家有爱用旧绢纸墨的习惯,因之遂使这项断代标准的下限,益发没有遮拦,这是格于事实无可奈何的特殊情况——因此,遇到了这种场合,上面所说的质料观察的断代须与其他的五项标准相辅应用方能有效,这在下面还要一一讲到的。
三、时代之习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习尚,虽天才超绝的大艺术家亦不易逃脱其影响范畴。正如汉朝的赋、唐代的诗、宋时的词、元人的曲…都没法易代而皆然。假如把元曲中的一支小令,却安置在董仲舒或贾谊的名下,明眼人一见即辨其伪。正如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只因其中多四六句法,分明是六朝以降的作品,便使人想到这绝不是汉代李陵的手笔在绘画风尚的断代上,亦复如是。
一幅“残山剩水”式的图画,却安在荆浩、范宽的名下,稍习画史的人,谁也不肯相信,因为是南宋以降,“马一角”“夏半边”才创出了这种短篇小说式的构图。同样,若把仇英画的一把折扇,却题归周昉或赵大年的名下,那也骗不住人,因为在唐、宋时代,折扇还没有“流行,画家大都是在团扇上表现其文采——这里所举述的二例,一是说明时代习尚之影响,一是说明器物形制的因时殊异,都是本章中所要叙述的断代要素。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上,他曾列举过器物形制上的实例来指正当代大画家吴道子等的错误:“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
“且如幅巾传于后魏,幂离起自齐、隋,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衣冠组绶,不宜长用于今人。芒履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这便是古人所见到的由时代器物上断代的好例。
唐代去古未远,吴道子号称画圣阎立本又是画人物的名家,一不当心还要闹出“不合时宜”的笑话。可知作伪者时代晚近,只凭空想去勾勒曩昔社会百态,要想处处不露出破绽,实在是戛戛乎难矣。因此,只消我们在这方面稍微用心,真可探讨出不少断代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来自画面本身,一旦提住“贼赃”,作伪者无所狡辩其时代——董作宾先生前些时曾以这样的方法来考证南宋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所得的结果便异常丰硕,真是这一方面成功的好例。
庄慕陵先生在《大陆杂志》15卷9 期上发表了一篇《唐阎立本绘(萧翼赚兰亭图)卷跋》,从标签上的记载,这自然是初唐时的巨迹,但慕老由器物上的研究,从辩才和尚坐的那张有扶手的靠背椅子上寻出了破绽——这种椅子在初唐时光还没有发明,所以不可能是阎立本的手笔,因为他没有见到,自然没法画出。因此,慕老由器物形制和时代的配合上一加考证,这幅画只能是五代时的顾德谦,而没法说是唐代的阎立本。
像这一类的例子极多,假如事事留心的话,真的是处处都可以有新发现。譬如说仕女的服装发式、建筑上的结构装饰、乐器执着的方式、各朝龙纹的画法,甚而至于碑趺龟首之上昂角度……一一都可以变成绘画断代的标准。
这项断代标准来自画面本身,又具体地人人可以指点,所以一旦得到结论,真的是嘉惠后学无量,值得我们好好地努力!若比起昔目鉴赏家的办法,用一个概括性的形容词,便笼统地描写了一个时代,如“唐人神韵、宋人丘壑、元人笔墨”等,那自然是有价值得多了。
前些时我也曾浪费了一些心力,依照着传统鉴赏家的款式,改拟了“唐人丰沃、北宋丘壑、南宋峭削、元人笔墨、明代造作、清人堆砌”的一套新体系来,并各为他们略作诠释:
唐人丰沃——这是指唐代画的人物,大都是丰满壮硕,画的马也肚大腿短,体态凝重,画的山水画也古拙宏拓,常有可以分裂为若干小幅完整构图的趋向。
北宋丘壑——指北宋山水画的丘壑重深,气势浑雄,实感逼人。这是我国山水画的黄金时代,历代鉴赏家所谓的“宋人丘壑”,意实指此。因之我也不予改动。
南宋峭削——南宋画风与北宋差别之大,实在更有胜过明、清二代之鼎革,所以需要特为标榜,才合实际。这是指马远、夏圭的那种小品精神:感觉敏锐、诗意浓馨、笔墨犀利,使我们有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情调,别是番新鲜峭拔的感觉。
元人笔墨——这也是原来的,因为很恰当,所以我们不去变动它。意思是说,元代大部分的画家,爱他们的笔墨更胜于爱大自然,只讲求笔墨的情调趣味,已渐失宋人在自然界中寻求实感的热忱。
明代造作——这是指他们距离自然更远,只钻进古人的法式圈套中,以模仿为能事。所以他们的作品都有点“纸上谈山”的虚伪单薄感觉,画面上灰污、庸俗、平板之意味逼人,所以说他们是造作。
清人堆砌—清代沿着明朝的路线继续走下去,既不观察自然,临摹古人的功夫也日见浅薄,几位号称正统派的画家,大都只能堆砌别人的山石树木,来它一个大拼盘式的凑合,所谓的“搬前搬后法”也,因此叫他们堆砌。
反而是一些非正统的画家,他们别有怀抱另开蹊径,却都有了意外的成功,石涛、八大就是显例。
以上这一套说法,对于一位初学看画的朋友,未必没有一点点新颖抉发的乐趣,但是我们以为:画风的转变未必和政治的鼎革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其次,选摘的字眼,未必就能恰到合处。把一代画风很扼要合适地用个形容词来指点明白,虽不能说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最后,四令找到合适的字样,别人的解释是否和你相同,那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只在篇尾以一种“谈助”的姿态括出说法,使大家知道“有此一格”就算是了。我们仍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具体的“器物形制演变”的研究上,因为那才是大家可用又少争论的断代尺度,值得我们尽最大之努力。
四、个人之风格
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大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上把他独特的个性,表现得格外显著。虽然时代之习尚,艺人没法摆脱其影响,但大同之中,不碍小异。掌握住此一要点,亦可以用为绘画断代之一助。
或许有人要怀疑:一位画家有中年老年之别,有兴会来否之异,我们能有把握地捕捉到他的独特风格引用之而为断代的尺度呢?——这不难释,正如大家的签名一样,由最严格的标准来说,世界上不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签名,心情有喜怒哀乐之不同,笔墨有粗细浓淡之差异,任何两次的签名都会有些许之参差走作,但是,不是么?这都不妨碍你向银行的提款!因为鉴别签字的专家,他具有一项独到的本领,他能从笔法的风格上去识别每个人的签名而绝少错误一一鉴别画家风格,亦复如是!
我国的鉴赏家所以要多看法书名画的原因,即在于此,仔细比较印证,反复审阅体认,一直做到了对某一位大画家的面目认识清楚,由外表的形似直到内在的神交,真是亲切熟识得如平生挚友。这样,当一画在壁伫立欣广之时,才能一览之下,如逢故人,立刻可以招呼出他的姓名别号。别人若有问讯,您可能够以“知己”的身份,将其个性特点一一介绍,这就可以发生断代的作用了。
古人也常用这种方法来鉴别流传下来的名迹,如董其昌在《宋元人缩本践画跋》(即所谓的《小中现大》)的第一幅山水画上,就这样发表了他的鉴赏意见:
“此幅相传为范中立,特以范山头多作蒙茸草树,有相似耳。顾此法乃不始于范,范画虽厚,亦与此幅门户不伦。谛玩之,其古雅简淡,有摩诘之韵,兼巨然之势,定是李营丘也。”(《故宫书画录》卷6,68页)对于该幅原画是否为李营丘,那是另一问题。但董其昌氏在这里所用的方法,就是由风格来断代的好例。一旦由风格上找到了画家那年代自然是随之而决。
由画家风格而来断代的例子,一反一正,我们列举出巨然《雪图》(《三百种》133图)和夏圭的《溪山清远》卷(三百种》115图)。前者的结论是否定的,后者则是肯定的。
巨然《雪图》的缩本亦见于台北故官博物院的《小中现大》中,而且临摹得很不坏。更有价值的是原画未毁,现仍在故宫,可以两相对勘,指点其中曲折原委。
现在试悬起所谓的巨然《雪图》来看,由画家风格上来作断代:既没有矾头和蒙茸草树,又没有我所谓的“散麻法,路径既不曲折隐显,苔点亦不苍茫浑厚,人物又过于纤巧,在在都表示出与巨师无关,应该是晚于北宋的一件作品,标签径标着五代巨然的名字,真的是不知从何说起。董其昌且在上面大书着负责鉴定的字样,也不知他是有何根据。
更有趣的是清高宗乾隆,一向和董氏不谐调,这次不知为什么,却在董跋之旁,御笔大书:“玩其林峦皴法,与王维雪溪同一神妙。”那意思不但赞成董氏的论断,而且就题目更在沙上筑塔,一直高攀到王摩诘门下,直是望文生义,随声附和,可哂之至!
《故宫名画三百种》的编者在申述理由之后,就不用巨然之名,而改标之为宋人,这自然是近乎事实得多了。我们希望用同样的这方法,把全书或故宫全部的画,都严格衡量一下重作标题,那不但是体例统一了,而且真的是功德无量。
夏圭的《溪山清远》卷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这幅巨迹的鉴定,一大半就建立在对画家风格的认识上。夏圭是南宋大家,以犀利之减笔斧劈皴作山水,清丽隽爽是其风采特色。在许多现存日本的夏圭小品及美国堪萨斯城艺术馆( Nelson Gallery of Art, Kansas City, Missour)中的山水长卷上,我们对他的风采已很熟悉,所以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长卷(8.89米)的鉴定,我们一点也不受标签的暗示,因为标签的题名,动辄在宋、元以上,早使我们深具戒心。同样,我们也不重视明人陈川的那篇长跋,因为根本就不在同幅纸上,伪画真跋的例子又是太多了。
我们所以相信这幅长卷是夏禹玉氏手迹的原因,仍是由画家风格方面着眼:这是所谓的“北宗”的画,也是属于“水墨苍劲派”的作品,大斧劈皴、减笔人物,笔致犀利清润,墨色多焦墨与淡墨之对比……在在都是南宋夏圭的面目风采。我们对这种风采神交已久,所以展卷快睹,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说比非夏圭不办!”——早于此尚没有这种画法(如李唐即较此繁细),晚于此的明朝戴进,又高跻不到这样的境界,既没有如此超脱的意境,又没有如此劲拔之笔墨。因之,由画家风格方面着眼,大家都口无异词地把这卷归属于夏圭的名下,而且还公认为这是他存世的第一杰作。
推测这幅长卷,当日应有签名,因为这样精绝的作品,画家不会忘记写下自己的名字,如今不见,可能是由于首尾俱有割截的原故——我在弗利尔艺术馆中见到一幅长卷,签标“马远《山水长卷》”字样;又在纽约都会艺术馆中,见到分截为两卷的“夏圭《长江万里图》”,那构图都和《溪山清远》相似而两端溢出甚多。可知这原是一张名迹,后来仿之者甚多。华府、纽约二本均是明仿,可知明前尚未截割。且作者有或马或夏之争,卷名亦有《溪山清远》与《长江万里》之异。可是由于风格之显著特征,大家都认为中博院所藏此卷,应题作夏圭,而且是存世第一夏圭。
既有上列的几项风格特点标举了出来,我很想对这位南宋大家的另张图画提出一点小小疑问,那就是有名的《西湖柳艇》(《名画三百种》114 图)。我国的鉴赏家一向有过于重视标签及题跋的倾向,这幅立轴的归名夏圭,大半就由于标签及右下角郭畀 之跋。问题是在这里了,我们到底是以画人风格为重呢?还是以题跋、标签为重?标签是后人所书,又多附会,其断代价值甚小。至于题跋,那就问题重,首先得辨其本身之真伪,即令是真,又其人之“眼学”亦当审察,最后得推究是否当日乃为势所迫,不得不作违心之论等等,真的是夹缠处处,疑窦滋多,远不如依据画上风格来做断代比较直接可靠。由于此,我提议幅《西湖柳艇》应该细加商讨,重作决我并不是说,已得确证,知道这幅立轴是另一位画家所为,不过显而易见的,由作品风格上来观察,与夏禹玉不谐。我只是在这里谦恭地作为个问题来提出,敬请高明的留意赐教并作“个人之风格”这一章的断代举例和尾声。
五、款章及题跋
画件的标签,是装潢时的附加之物,和画件本身的关系可以说是远门亲戚,但画件上的名款和印章,却是鉴定真伪、判断年代很有用的直系亲属,值得我们多多留意。
我们都知道,在五代、宋初,图章尚不风行,画家每每只在画上签上个名字便了。如有名的《江行初雪》卷一开头就有“江行初雪,画苑学生赵幹状”字样,既在同幅绢上,又画名、职名、姓名三者俱备,所以保证作用异常重大。同例《万壑松风》巨轴,远峰上写着“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的题款,有时代、年份、季节、籍贯及姓名各项要素,都是很大的保证。其他如《双喜图》(《名画三百种》81图),树于里写着“嘉祐辛丑年崔白笔”;《早春图》(《三百种》76图)有“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并有“郭熙画”一印;《溪山楼观》(《三百种》71图)上有“翰林待诏燕文贵笔”等字样,审查笔法同墨色,都是画人原迹款章,所以保证的作用很大。
宋代的画家,他们对自己的签名,有“保密”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徽宗帝可以称例外,大约这是由于他身份不同的关系。)他们大都是把名字签在山边水涯、石隙树缝等处,使人若不若意寻找,便不能发现。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上的本人签名,竟和我们捉迷藏了几百年之久,一直到最近才被发现,便是好例——这巨轴很久以来就被记载作无名款,却于三十七年八月中被我找到了范宽二字的签名,深密地躲藏在丛树的叶隙中,于是这幅画的真实性就得到了新的有力保证。
由上面的举例,使我们想到,签名题款的格式,亦有其时代演变的迹辙,若对之研究清楚,正是对古画断代的得力助手。
就现所知的资料,我们用考古学的方法,可以对款章的格式演变,依照年代次序,描叙如下:最早的画家签名,是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的《女史箴》卷,那上面有“顾恺之画”四字名款,但其真确性很有问题,孤证不立,这一段暂时从阙,留待新资料之发现。
唐人的签名尚未发现,《双骑图》(《名画三百种》17图)上虽有韦偃签名,但画的本身就有问题,不能作数。刁光胤的签名亦待商榷,所以没法描述。下降五代,荆、关、董、巨都未见到他们的亲笔签名,所以我们猜想,是不是那时的画家,尚没有在每一幅画上都留签名的习惯?米芾在画史上说,曾见到“洪谷子荆浩笔”的签名,但那真假与否,如今已不复能按图指证了。
五代之末,下及宋、元,可靠的签名资料,发现渐多:赵幹的签名在卷首(《江行初雪》),范宽的签名在叶隙,郭熙的签名在边缘(《早春》),崔白的签名在树干(《双喜图》),燕文贵的签名在山崖(《溪山楼观》),李唐的签名在远峰(《万壑松风》),萧照的签名在悬崖树阴下(《山腰楼观》),林椿的签名在花叶下(《秋晴丛菊》),马远的签名在左侧(《山径春行》),赵大亨的签名在石缝中(《蓬莱仙会》),李容瑾的签名太靠近右边缘了,竟被裱工切去了一半(《汉苑图》,《名画三百种》175 图)……可知这阶段中画家的签名有躲藏的习惯,有时不签名,签名时亦爱放在隐秘或人不注意的所在。
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下列两端:一为藏拙,这是他们的谦逊美德。一为统一,他们不愿意以显著的字迹来破坏整个画面的气氛。
元代以后的画家,逐渐重视笔墨的趣味,由于书法和绘画在用笔上的意趣相通,书法就逐渐渗入了画面。最后且成了画面上的要素,甚而至于一幅画上若没有题字,简直就不大像幅中国画似的。这就是题名款识在画面上的沧桑历史。
宋末元初的钱选、赵子昂两大家已开始了在画面上的题字的例证,如钱氏的《贵妃上马图》,现藏弗利尔艺术馆,那上面就有:
玉勒雕鞍宠太真
年年秋后幸华清
开元四十万匹马
何事骑骡蜀道行
——吴兴钱选舜举
的款识。赵孟頫的《二羊图》《双松平远卷》,不但款识俱有,而且就画面大做其议论文章,这就表示在那时候,文字已侵人了画面,行将与画共同组结全幅的构图了。
这种倾向黄子久、倪云林都有,但最显著的还是梅花道人吴仲圭,他的草书苍茫朴厚,时常长篇大论地写上画面。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文礼博士(Dr.A.G. Wenley)曾把他们的收藏《风竹》立轴写了一篇专文,由这上面可以见到这项演进的过程。因为这幅画的题字和画实不分割,画家虽然是有意地要融化这二者于一构图之内,若去掉这几列通天彻地的长行题识,那不但风竹为之减色,同样,也破坏了作者构图意境的巧妙完整——这可以说是一个分界里程碑,后来文人画的满幅题字或竟字多于画的构图都是这一脉流传而下的,是绘画史上题识部门中的重要事件。
上面所叙述的签名题识沧桑进化史,亦大大有助于我们对古画的断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系统在我们的意识里,若遇到了“不合时宜”的签名题识,那是会触发我们的警觉的。下面说的《十全报喜》(《三百种》106 图)就是一例。
这幅画的鉴定,主要的是靠它左侧的一行题款“画院待诏林椿画”。我们也是由此生了怀疑,这分明不是南宋人题画的字体和格式。椿字写得太小,其他的字又写得太大,在在都成问题。再与《秋晴丛菊》上的林椿签名比,那笔致虽然与此不侔,椿字也没有忽小一号的倾向,那《十全报喜》之为伪作的可能性就更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这幅巨轴上的画法,笔墨淋漓的味道过重,分明是元以后的作品。绢又不像是宋绢,因为幅面是太宽了。题跋的保证又太新,这样各方面来综合地一加比较,林椿的这幅《十全报喜》,在我个人的断代研究中,似以归之于明人为近乎事实。不知大家亦以这项说法有道理否?这即是由款识而作断代之一例。
印章的发展史亦有点像款识似的是很危险的。因为印章可以伪作,古印犹有孑遗,若对印鉴的相信过了限度时常会上了作伪者的大当。
再退一步讲,即令印章是真,但是若无其他旁证,如款识等之存在,单凭一颗印章,你也没法决定它是画家之章或收藏之章。如所谓的巨然《秋山图》(《名画三百种》45图),董其昌氏将“梅花庵”一印鉴定为“收藏之章”,所以他题作吴仲圭所藏。赵孟頫的《鱼篮大士》(《三百种》149图)上有赵氏子昂一章,收藏者却把它当做画家之章——若依我们看,若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辅助,随便你怎样解释,都是只有二分之一的可靠性,那就是说,你可以解释作是画家章,也同样理由充分地可以说它是收藏章。
若用“看画第一,印鉴辅助”的原则来平心衡量一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二幅画都是判断错了。从笔墨上看《秋山图》确是吴镇的个人风格,试与吴氏之《清江春晓》(《三百种》162图)等图一比便知,所以那颗印鉴,倒是画家之章,不知是董其昌先生看走了眼还是难却姚公绶之情,或势有所迫,才闪烁其词地在上面题成了巨然。
《鱼篮大士》一像,笔墨平卑,衣褶用线犹豫重复,滞凝无力,只是明代匠人之作。赵氏子昂一印,不但不能解作画家章,就是退一步解作收藏章亦势有所不能,因为赵氏眼高于顶,没有收藏这种劣画的道理,这里面必定还有丘壑——所以只凭印鉴而遽作鉴定,绝不是一条安全的道路,这在本文的结语中还要说到的,所谓“孤证慎立,综合取断”是也。
题跋是画的附件,它是画家的友人或后来的收藏鉴赏家对作品的记事或赞美。由于日月的推移,到后来变了史料,因而可作断代之助。许多因其原名佚落,或原来就没有签名,那可靠的题跋就时常给我们带来了用的线索,如《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三百种》第124至126图)上的宋濂一跋就对我们大有用处。同样的,宋徽宗对黃居寀《山鹧棘雀》和郭忠恕《雪霁江行》的题字,亦构成我们信赖的一项重要凭依。
在这里是得注意“真画伪跋”和“伪画真跋”的有意骗局。这是字画商人故弄的玄虚,他们用“以画证跋"接“以跋证画”的手法,好达到他们一物卖、获利双倍的目的。这里边的要点注意画本幅和题跋接衔的关键,若在同一幅绢纸上,或各代各体字迹俱备(这是指题跋者多的话),那可靠性就比较大;反之,若二者不在同一幅面上,又没有其他证明知道它们原在一处时,那就是需要特别的留心判断了吴爽秋先生曾对我讲:黄子久的《天池石壁轴》(现藏故宫者)就有这种现象发生,你看他边缘上的题跋,都是真的,但画件本身孱弱琐碎,分明是赝品,这是假画真跋的例证。
真画而附有假跋的例子太多了,真是不胜枚举。这多半是著录上有某某题跋而被移作别用,不能不在这里依样葫芦再描一番来充数的,如伪造董其昌跋语的画件很多,《富春山居图》的卷子有两个,而两卷上都有同样的董跋,依理推测,那必有一个是伪作的。
最有趣的是李成《瑶峰琪树》册页(《名画三百种》第62图)的对开“伪”跋,这题跋确是董其昌写的,但与李成和《瑶峰琪树》无关,因为是张冠李戴地移植在这里,原为一小条幅,现在因迁就册页的形式,就被剪贴得十分凄。我们若肯费上一点心思,很可能再把这题跋重复旧观。吴讷孙博士是研究董其昌的专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董跋的毛病。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伪跋”,对画件本身的鉴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综揽论结,款章题跋在绘画上的断代是有其功用,但亦有其限制;最好只拿它们来做辅助的旁证,而不要用作积极的主断——一幅本身很好的画,款章题跋可以助之相得益彰。反之,若画件本身无足取,虽有好的款章题跋(签名在这里自是分量较重),我们引以为证时亦当特别审慎。因为签名的真伪,有时尚可分辨,但印章题跋作起伪来,虽专家们亦受其欺蒙。因之我们不能不小心从事,不然,以偏概全,反客为主,那是会使我们得到错误的结论的。
六、流传与著录
国的历史资料最丰富,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画著录很多,无疑义的,这都是有助于断代鉴定的好资料。譬如说我最近为《明皇幸蜀图》作一展拓的新研究,见到唐明皇的图画就做记录,不多时,略一统计,见于著录的就有四十件之上,内中至少有九件尚存今世这都是画史著录对我们研究方面的伟大功用。
如在《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上,对于《明皇幸蜀图》有这么一段记载: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团扇,绢本,设色。宫殿连延,花树掩映。中道赭袍按辔者明皇,徒步前导十余人,提灯擎扇从骑二人,贵嫔宫监二人。贵妃乘玉骢,力士仆役数人,西幸出宫,风景仓皇。图左古印莫辨。据对题诗,此图为幸蜀初出都门事。《宣和画谱》载,昭道又有《摘瓜图》,乃幸蜀道中时事也。
○侍儿扶起跨金鞍,圣主频频顾玉颜。两出都门犹并辔,奈何掩面马嵬山。
唐苏灵芝行书,对题。团扇。绢本。”
像这样的著录,对我们十分有用因为它把一幅唐画的布局,包括背景及人物动态都描述得很仔细,我们读了这项纪录,已能在脑海里描绘出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来。记得是在《大陆杂志》9卷1期上庄申兄引用了这篇著录,那时候我想,以此项著录之详细,以故宫收藏之富,虽李昭道原迹因历时过久,不一定还有遗存,且我国画家都有临摹的习惯,说不定会有仿本会给我们发现出来。如有名的《王会图》《击壤图》,不是在《故宫书画录》的简目中都有记载么?不得已而求其次,仿本的发现,对画史的研究亦是极有用的。
果然猜想得不错,今年秋天陪同高居翰博士( James F. Cahill) 看画的时候,在故宫的宋人合璧画册的第关上,有题作郭忠恕《宫中行乐图》的幅“团扇”,那上面正是画的“宫殿连延,花树掩映,贵妃上马,明皇回顾”,两相印证,真的是若合符节。于是一幅名画的面目,千百年后,又得重供吾人推索,真是画斋抉发之乐,南面王不与易也。由此可知著录之嘉惠后学,实在是深厚而博大。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文献著录,实在是研究断代之重大资产与成功之保证。
另一个例证可举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卷,这卷子现有两本,都在故宫博物院。一即所谓之子明卷,题赠子明隐君者;一为无用卷,为无用师所画者。
乾隆先得子明卷,由于签上只有“山居卷”字样,他还有点怀疑。后来又得无用卷,两相印证,那才知道二者构图相同,都是所谓的《富春山居图》卷。那么二者之中,哪一卷为真呢?正是所谓的“先入为主”,乾隆皇帝一直认为子明卷为真,带着它到处巡狩,每当兴会来时,便在上面题识,只把这一长卷的空隙都添满填尽,然后才在前隔水绫上心有遗憾地写着:“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他自然是兴犹未尽,却没想到简直把这画卷给摧残完了。
现今的形势,大多数的专家都承认无用卷为真本或较优本(这项笔墨官司很可能还要打上一些时间而不得解决),因为那上面的题识与曹知白《群峰雪霁》上黄氏题跋的笔致相似,是较优于子明卷的一项旁证。
更有一项流传上的见证是:无用卷上有火烧痕,而子明卷上则无。据流传的记载,吴冏卿临死时候,曾把《富春山居图》来火焚殉葬,他的子孙从火炉中抢救了出来,所以便有了连续间隔的火烧痕。因为卷子旋紧了,只能先烧透一个窟窿,展开来,就在等距离上都现火烧痕了。
以上所说,是艺坛流传下来的掌故,这虽不足以证明无用卷确为真本但却证明了这是经过明代吴冏卿所珍藏的那一卷。学术性的研究,如筑宝塔,在坚实的基础上一层一层向上堆叠。有这一项证明,我们就可以拿这重做起点,再向深处研寻,这就是流传著录有助于断代的一例。
另一项流传著录的好例,我推荐所谓的《小中现大》,因为不但有题跋考证,而且附有缩本的图画,这比只用文字来描写,自是逼真且有价值很多。
在这册22幅的缩本图画中,有巨然《雪图》和范宽《溪山行旅图》的原迹,现都在故宫可以展图对勘。对照的结果,知道缩本的描画,态度非常忠诚,功力亦很深邃,不但画面绝端相似,题跋也都一字不差。很像是当日有人携画请董氏鉴定,他每遇名迹,便临一缩本,并把自己在原画上的题跋一字不误再抄上去,因为若不如此,怎能如此地毫发不爽?——吴讷孙先生、王季铨先生都说这是王时敏的临本,临成之后,再去请董其昌题字,在王原祁的画语录中说到此事。我自是尊重专家的意见,而且觉得很有趣,由画语录证小中现大,由小中现大的证古代佳作,都是流传著录有助于断代的好例。
从这22幅宋元名画的缩本上看来,其中一大部分原作显然是不在人间了。那么,这一巨册著录就有两种大的功用:一是假如原画突兀出现,这本著录就是有力的见证;二是假如原画泯灭了呢?幸亏有这项纪录,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溯原作的大致典型——这种流传著录的功德永可感激,因为许多艺术史上关节桥梁,都因此而得寻溯不然,一个环扣的脱节,那会使若干重要的现象都没法解释的。
总之,我国的画史资料丰富,现今画件庋藏的情况又很集中,条件已具,前途大有可为:以古画印著录,以著录辨流传,上下贯通,左右逢源,真的是如见古人,时有新得,与名画为友,借典籍为师,披览欣赏,冥会抉发,个中乐趣,真不足为桃花源外人道也——譬如说,大家都知道波士顿美术馆近来得到一张关仝的画,由这幅巨轴山水来看,所画的松树都“凰尾翩跹,不见细干”,这就使我们想到画史上的著录关全“石树出于毕宏,有枝无干”真是若合符节,多么有趣!若再加上南唐李后主的金错刀题字和赵孟頫的跋语,使我们知道这就是《宣和书谱》上著录的“崖典醉吟”,赫赫名迹,流传有自。画史上又说关氏不善人物,每使胡翼代笔,那这幅画上的人物不又是胡的仅存杰作了么?——如此印证挟发,千百年历史沧桑,各大家墨彩妙迹,数千卷流传著录,一时并臻心下,真的是不知人间更有何乐!若环境准许或助我们循此长往,中国艺术史的重新写定应该是极可乐观的。
承曾宪七先生的雅意,特用航空将这幅《崖曲醉吟》寄来,谨在这里向波士顿美术馆、富田先生和曾先生致谢。我尽快地在这里公诸同好,使大家都能“先睹名迹影本为快”。并且就题发挥,略略说到了一些流传著录的印证,以作本章的结束。
结语
由朋友叫我鉴定一幅古画说起谈到了中国绘画的断代问题,由我暂拟的六项标准(这可以称之为中国画的“鉴赏六法”;从前我写的那篇《中国绘画的六法新论》,可称之为“欣赏六法”),说到了中国的画的通盘整理。再从“近代史料的第五发现”讨论到中国文化史的更丰满,旁涉到世界艺坛之澄清题目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为了避免汗漫无归的毛病,不能不在这里原始要终地来一个简要的结语。
世理原是平坦放着,但有时最常见的反被略过。谁不知道古画是史料, 但一向都只被人欣赏,却忘了它们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第一等物证。如今拈出,说这万件古画是近代史料的第五发现,平心思考,其实不谬。
一旦道及真理,证据齐来拥护。古画既是史料,用治史的科学方法必能整理得清楚明白,使以往的混沌局面一扫而空。这种方法在学术界的各部门中都奏了宏效,中国艺术史的正确写定,必可乐观厥成!
一块学术新园地的开发,疆域宏阔,前程远大,是其长处。草莽初开,阻碍丛生,厘立论断,遗漏滋多,是其所短——绘画史新园地之开辟,亦复如是。所以上列各论,都是草稿性质,纵横捭阖,先指点出这新王国之四至及前程,然后集思广益,删改增订,以期于精密,这样,就可以截长补短,共策这一件大事的成功。
六项标准一立,是条目已张,从此论画的鉴定,先有这样的依据在手,可以逐条验证,不致落于空玄,这是新旧方法的划界,保证了我们不再落于混沌难解之圈套中。现在是以分析始,以综合终,其始也小,成就却大,不久即可望见到这一桩新事业成功的报命。
上面所说的“鉴赏六法”,因为要说得清楚,所以只好逐条分析。在这篇结语上,为补救这项短处,再给它一个通盘思考,使知道这原一个整体的随机应用,只要在某一点上得到正确的线索,就可以综合地紧追不舍,一直探寻到可靠的结论。为此,我对这六条标准的综合应用,预先思拟了三项应该遵守的原则:
A.“本体第一,附件其次”——此即所谓的“看画本身最重要,印章题跋居其次”。这很容易义释,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画,就它本身找证据,自然是比在它的附件上找证据要可靠得多,要重要得多。
在前面所说的断代六法中,它们各条的重要性显然不是平等的:质料是画件之所凭借,技法是作品之所形成。一幅画不能脱离其时代之影响亦不能没有作者的笔致风格,所以由第一项到第四项都是重要而直接的。
在第五项的款章题跋中,作者签名的重要性又凌驾其他细目之上。但许多好画没有签名,我们仍旧有法使之归队,印章题跋亦然。第六项的流传著录只是记问之学,也可以说是画件的“身外之物”,以之作印证考据是可以的,若以之当作画件断代之主证,随时都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两项标准,列之为次要间接的资料或是辅助的资料。
在一幅画的断代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总是尽先使用那些直接的资料,如:这是什么时代的绢纸,这是何种特殊之画法?在器物形制上有何时代之特征?在风格上和哪一位画家最相近似……这样思考过了,再用间接的资料来作辅助,去考究上面的名章题识跋语,有疑问时又检出著录来考证它的流传经过……最后,再综合权衡而得结论。
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出入主奴”的成见歧视,却正是名画鉴赏的中庸大道。因为若不锻炼出一些真知灼见,到头来只随着标签印章脚跟团团而转,那是极可惋惜而又极危险的事——国人受这种坏影响的程度,还较外国朋友们为甚,因为他们对方块字的认识不深,所以爱用“就画看画”的办法来断代,因此,他们也常常有新的见解使国人瞿然自醒,我认为这种办法是值得推荐的。
标签的不可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题跋的真伪亦因装裱摹拓而变得扑朔迷离,若不幸受了它们的暗示,养成了“强画面就签题”的坏习惯,那浩如烟海的中国画就难得清理出一个头绪来了一若用“本体第一,附件其次”的原则来断代,这项国人易犯的毛病就可以避免,因列为原则第一。
B.“孤证慎立,综合取断”——意思是说:只用一项标准而遽作断代是很危险的,必须和其他相关各项综合应用然后下的判断才可信靠。
这也容易解释,孤单的证据容易作伪,一下子没有辨别清楚,很容易受骗而作了错误的判断。但是,若仔细审察多方面的证据,那错误的机会自是较少。
以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例:画绢的年代对,拼接的方式合,不但气势深雄、丘壑重深确是北宋气魄,而且矾头丛树雨点皴法都和艺人风格相符,签名隐秘,确合宋人习尚,墨色沉重,亦与流传著录相合。又有董其昌题字及王时敏题跋之摹本以作佐证,于是上述六项标准具备。然后我们才下判断说:《溪山行旅》一图,确定北宋范华原所作!——这样,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定点,才算是确切可靠地为我们所找到了或许有朋友要说:这样太麻烦若每一幅画都要如此的仔细平章,那什么时光才能把中国的名画清理出个头绪来呢?
——这不须忧愁,严谨的方法正当如此。第一,依此标准长日做去,熟能生巧,所费工夫并不像所想象的需要那么多。其次,可靠的历史定点,或一位作家的代表之作,都是那时代的顽标尺,使命特别重大,故需最审慎的考证。一旦若干定点建立坚实了,那周时代的作品就很容易处理,不再需要同样多的时间。
上面说的是综合取断。孤证慎立的例子就太多了,前面所叙述过的巨然《秋山图》和赵孟頫的《鱼篮大士》还有所谓的钱选画的《卢仝烹茶图轴》(名画三百种》127图)、吕纪的《草花野禽》(《三百种》217图)都是应该仔细商榷的作品,仅凭一方印章或一篇题跋而遽作断定,在独证慎立的原则下我们都认为不是顶妥当的办法。
像上面的例子真不知有多少,我们要把心中打扫清净,放弃成见,摒绝暗示,由可靠的立脚点逐步向外推断。不作高论,不求速成,把现存世间的我国名画,从新评审,妥为安置,使它们各就本位、各得其所,那对中国绘画史的重建,才会有最大之成就。因把“孤证慎立,综合取断”列为原则第二。
C.“时尽最早,代取最晚”—这就是说,在一幅画面上若没有晚期的因素发现时,时代应尽量定早,反之,若画面上有不同时代之多种因素发现时断代应取其最晚者。
前者是为矫正近来的一种“偏激倾向”。这和用新法治史的初期现象一样,也有所谓的疑古学派。当初看画,多是信古,标签所云,当有凭依,所以是径信而不疑。后来材料发现多了,例证有彼此冲突的现象产生,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疑古画派。他们对我国古画采取一种过度怀疑的态度,遇到幅古画,总爱把它说成假的,一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谨严,一以表示自己的眼光高超。
信古与疑古二者,在我们看去,正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如今我们提出这项“时尽最早,代取最晚”的原则就是要免去他们的矫枉过正。
如所谓的元人《宫乐图》(《三百种》第204图),这幅画虽被标为元人,但细寻其绢地、色彩、画法、器物形制,都没有晚期的因素发现。若依我们“时尽最早”的原则,这画应列入晚唐或五代的规格之内。如今一标上元人,虽有所注释说明,观者不明就里,每每已受了错误的暗示,不若把时代标早,留待日后验证。——若日后没有资料发现证明,这确是晚唐、五代人之作,那我们没有埋没英才。若有新证据知确系后人仿制,那时再来改正,亦不为迟。
若一幅画面上有几种不同的时代因素发现:甲因素表示这画可以早到北宋,乙因素说只能到南宋,丙因素又指明这是明初人的手笔,那我们对这画的断代就取其最晚者。这理由大家都一目了然,北宋绢,南宋画法,明朝人都可以支配习用,而“宋版的《康熙字典》”是不能成立的。
仍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为例:画面上一片唐人风采,但“钉头鼠尾描”的因素发现了,表示它不能早于北宋武洞清,因人断代,这画就只是宋仿而不是唐作一乾隆皇帝曾在这画上题诗,末两句是“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如今依我们“代取最晚”的原则,那这幅画就只能是北宋而不能近乎唐了。
六项标准,三点原则,都已陈述如上,例子也举过了,只剩下一点尾声在这里一并向大家做最后的呈献。
首先我得请大家原谅我举“例”的限制。以存世古画之多,有关典籍之富,区区二三万字的一篇文字,实在没法举例周详,所以这篇文字真的是中国画断代研究“例”,希望这些例证都能举一反三地广为引申,使这篇初辟草莱的文字能逐渐周全,到最后提示出我国绘画史新时代之来临。
其次我当略费言词祛除一些朋友们对这项工作的某些过虑。有人曾想到艺术品经这样一分析解剖,像走了气的酒一样,那还有什么神秘美妙的味道呢?
这无须过虑:史料用科学方法分析,艺术用综合感觉享受。对于一幅画的鉴定,是科学的,有这篇“鉴赏六法”在。对于一幅画的欣赏,是文艺的,有欣赏六法”在。这二者正如鸟之二翼、车之二轮,一为求“真”,一为求“美但这二者综合地有一个目的,在止于至“善”!—谁会见一个人变成了地质学家之后,便对黄山、雁荡山等山川之美再也不能领略?只怕适得其反,他因了解得深,更比平常人一千万倍地热爱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呢!
最后,我响应胡适先生等“把汉学研究中心建在台湾”的主张,而且更进一步地提出“把研究中国画的中心在北沟建立起来”的口号来!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画的收藏中心现在故宫,画件不能离开它的博物馆,那研究的机构势非“移樽就教”不可。我们总希望一个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所有一天能够在北沟创办起来。资料既丰,经验渐足,只需方法正确,得人以赴,十年之内,必可有成!
现今世界上研究中国画的情况是:概括性的介绍时代已成过去,如喜龙仁氏七巨册的《中国绘画》(Dr.Osv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就是这一阶段之好例。现今的西方学人,早已开始用他们的严谨方法,对能得到的中国名画做了细密的研究,如Lau rence Sickman, A.G. Wenley, Sherman E. Lee, Aschwin Lippe, Max Loel James F. Cahill, Richard Edwards等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日本的学人如富田幸次郎、岛田修二郎、米泽嘉圃、铃木敬等,国外的中国的学者如耶鲁大学的吴讷孙先生、波士顿美术馆的曾宪七先生、普林斯顿的方闻先生等也都是各有专攻,各有成就。这可以说是已用新方法对中国画展开了正式的研究。借用军事学家的术语,对中国画的园地已展开了据点的攻击。
所以这一方新园地的全局,清晰如画:玄学式的迷雾已经消散,鸟瞰式的空中侦察业已过去。现今大家的战略是稳扎稳打,就坚实处重新下功夫已经开始了“点”的攻击。计划着集点成线,展线成面,最后的目标是中国绘画信史的重新写定,好为中国的文化史增添一颗美丽的钻石,好为世界文化增添一派“光华复旦”的灿烂光辉。
我们身在宝岛,对祖国文化系念弥深,为守藏吏,更感在这一方面责任重大,所以就浅见所及,揭橥出这“鉴赏六法”来做及时的呈献,希望这项有关我国文化及世界艺坛的研究,它能立论有据、谬误有正、扶持有人、成功有望。
本文承庄慕陵先生赐阅一过所指正,又蒙特准引用其珍贵资料,谨致谢忱。
又索予明兄及庄申兄校阅原稿时,匡正良多,一并致谢。
许多师友都会看出本篇的命题是在仿效董彦堂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我坦然承认这项猜测的正确,因为这里面原有一番深意存在:第一董先生是霖灿生平最景仰的人,所以高山仰止,愿仿效之。其次,本文列入《董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以规摹之作,为先生寿,异常应景合宜第三,彦老那篇巨文,已被公认为甲骨学上划时代之作,本文虽谫陋无那,但也有相似之远瞻壮志。只需大众不弃共举此“鉴赏六法”而赐教之,则“科学的”中国绘画史必可从此建立。面对着这一万点绘画史料的大宝藏,缅想着不久在外双溪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展望这片学术园地的新前途,真的是信心坚沛,忻企无量!
资料来源:薛永年主编《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8月第二版
李霖灿(1913-1999),河南省辉县人,艺术史家,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自1941年始在国立中央博物馆工作,1984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职务上退休,毕生从事艺术史研究,并在台湾大学、台湾师大等校任教中国美术史及古画品鉴研究等课程。其著作有《中国美术史讲座》、《中国名画研究》、《山水画技法、苔点之研究》、《中国画史研究论集》等。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前半生玉龙看雪,后半生故宫观画。”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dacesmiling@qq.com